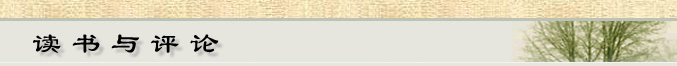黄山书社于2006年3月出版了高寿仙先生的新作——《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全书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史论结合,评述严谨,是作者近年来对明代农业问题研究成果的总结。出版两年以来,是书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张德信、林金树、封越健等著名学者先后撰文评述。笔者不揣浅薄,也欲将读书心得罗列于下。
首先从选题和内容上看,作者以明代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充分体现其立足学术,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
我国自古就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一直占人口绝大多数,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然是决定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现实情况有其长期发展形成的复杂性和连贯性,故学者一再强调要“放宽历史的视界”,对现实情况作“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明王朝作为帝制中国晚期重要的大一统政权,其农业发展水平接近于传统社会的最高峰。虽然没能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时代的嬗变,但明代中后期在农业经营和生产关系方面也确实出现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气象”。因此,作者选取明代农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无疑是追求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审视。
全书33.8万字,共分5章。其中某些章节探讨明代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额、土地形态与生产关系等学界长期关注,争论较大的问题。作者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史料,提出全新观点。在论及明代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等问题时,作者通过利用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理论解读文献史料,得出极富现实意义的结论。
此外,本书有如下特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1、善于总结前人成果,把握学术研究动态。
学术研究是一种不断积累、总结前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建、有所突破的过程。本书最大特点即是很好地把握了前人成果与自身研究的关系。以本书第1章为例,作者针对《明太祖实录》、《诸司职掌》、《明孝宗实录》、正德《大明会典》、《后湖志》、《万历会计录》、万历《大明会典》等明朝官方文献所记明代田土数字前后矛盾、出入惊人的现象展开讨论,认为明代农耕田土应包括官民田、屯田、庄田、不起课田、隐漏田,再去掉山塘面积,并估算出洪武末年、弘治末年和万历末年耕地面积分别为466万顷、558万顷和916万顷。(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25页。以下引用该书之处,仅注页码。)而这些数字正是作者在对清水泰次、滕井弘、杨开道、梁方仲、顾诚、郑克晟等中外数十位学者的观点进行详细分类、总结和考辨,并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再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因而颇具说服力。再如本书第5章,作者梳理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模式和问题意识的嬗变时,将二战前后至今的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情况分为三个时间段,即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的“商品经济论-地主制论”、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乡绅论-国家论-共同体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经营生产方式论-地域经济论”。其间对数十位日本明清史家的主要著作和观点分类总结,为我们了解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现状提供了极大方便。
2、征引文献丰富翔实,论证有力。
傅斯年先生曾提出“史学即史料学”的著名观点。此语道出了史料作为史学研究“食粮”的重要意义。本书征引文献极为丰富,仅方志一项便达百余种,其他正史、政书、实录、奏议、文集、笔记、小说等史料也达数百种。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史料并非简单引用,而是通过认真考辨,发现其中很多错漏和不被前人注意的问题,进而直接形成了令人信服的论据。比如本书第1章关于洪武年间的户口数字,以往史家多以万历《大明会典》记载的“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数作为研究明初人口史的依据。作者通过比较《诸司职掌》、《明太祖实录》、正德《会典》、万历《会典》等文献的依存关系,得出“根本不存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数”的论断。作者指出,万历《会典》“凡例”中明确规定:“凡《(诸司)职掌》旧文,俱称洪武二十六年”。而《诸司职掌》所记其实是洪武二十四年第二次大造黄册,并根据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的数据适当调整得出的数字。正德《会典》和万历《会典》都沿袭了这一数字,万历《会典》便按照“凡例”将这一未注明年月的数据系于《职掌》纂修完成的洪武二十六年。(第26页)这一发现,正是作者充分把握基本史料的结果。
3、观点独到,勇于争鸣。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目标之一。本书作者在充分把握史料和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新观点。比如,在考察传统中国乡村领导阶层和权力结构时,作者借用现代学者所提倡的“地方精英”概念作为地方社会领导层的代称,并根据明朝社会政治结构的具体情况,将明代地方精英划分为“职役性地方精英”、“身份性地方精英”和“非身份性地方精英”三大类。以此为切入点,详细讨论了地方精英同政府的关系等问题,给学界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再如作者提出明代农业在土地开垦、经济作物种植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交互作用,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灾害的发生频度日益增加。这些研究无疑都是极富现实意义的。
学术研究贵在争鸣,作者对中外各家观点既有提倡又有商榷,合理对待前人成果,不盲目相信权威。如本书第5章对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傅衣凌先生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的介绍,作者认为傅氏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但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和表现、中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值得商榷,并指出这是受当时学术和政治环境局限的结果。值得钦佩的是,傅氏晚年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对“变迁论”中的基本观点作重大修正,本书作者对此作极为推崇,认为这篇傅先生的反思之作极富创建意义,反映了老一辈史学工作者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
此外,作者还对美籍华人史家黄宗智和清华大学著名学者李伯重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分别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给予详细介绍和评述。黄宗智将明清以至1949年以后的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经济表达为“过密型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高氏称之为“缺乏有效制度创新的增长”。)正是由于在制度方面没有发展出适当的模式,中国经济长期在伊懋可(Mark
Elvin)所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中挣扎而无法脱出。明清时代的变化主要在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面积增长的速率,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我国采取的措施是大力提高土地单位面积收入,而导致的结果是土地收入的增长低于劳动投入的速率,即“过密型增长”。李伯重起先对黄氏“过密化”理论推崇备至,认为这一理论是“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但随后李氏开始质疑黄氏理论,认为“过密化”并不适用于1850年以前的江南历史实际,其“最低生活水准”和“人口压力”说也值得怀疑。他进而提出,“过密型增长论”是对帝制晚期中国经济模式的曲解,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真相应该是“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所谓“斯密型成长”,是与“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和“库兹涅茨形成长”(the
Kuznetsian growth)
相对的概念。根据美国学者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的解释,“广泛性成长”主要是由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数量的增加推动的,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斯密型成长”主要是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的,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库兹涅茨形成长”主要是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的,不仅有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明显而持续的提高,而且还有重大的和不断的技术变革。李伯重认为:“18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不仅动力相同,而且归宿也相同”。也就是说,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它主要表现为工业与农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而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又是通过各地之间贸易的发展而达到的。
以上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前沿理论,本书作者向我们介绍这些理论的同时,认为黄、李二人的论断都触及到了关于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难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二人的某些观点也值得商榷。比如,他们都试图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发展的独特性,但并未跳出“停滞论”的范畴,而李氏对“人口压力说”的质疑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此作者一再提醒我们切忌走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而忽略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共同性的那些经验和特征。(第266页)
高寿仙先生早年就学北大历史系,从著名史学家许大龄先生治明史。几十年来,秉承其师门严谨扎实的学风,长期关注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前沿理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相当影响的学术论著。这本《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就是高先生撰写的又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优秀著作。当然,我们在认真研读本书,学习其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对书中某些观点还需进一步推敲。比如第一章关于明代人口数字研究。作者首先估算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直隶及13布政司人口数为6807万余人,再加上218万卫所军户人口、30万带管民籍人口,共计7055万余人(第38页)
。随后,估算明代人口增长率为每年0.5%。这样,以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总人口数7055万人为基数,乘以0.5%的年平均增长率,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达到1.9亿人,作者认为这个数字大致可以视为明朝的人口峰值(第44页)。这样的估算结果和计算方法是否合理呢?据作者称,他的计算方式是学界“最常使用的方法”,即“通过检验有关数据推测出明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再以洪武后期的全国总人口数为基数,推算出明代后期的总人口数。”(第39页)目前学界对洪武后期人口总数的估计和明代人口增长率的估计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对明代人口峰值的估计也相差极为悬殊。而作者虽使用大量篇幅论述目前学界几种主要观点的得失,并试图探索一套更为合理的计算模式,但由于资料本身所限,难免还是有一些“大胆假设”的成分,仍无法让人完全信服。“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有时采用推测的方法亦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随意改动原来数字的做法,是否符合科学性?”(林金树:《评〈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明代史料中的数据缺漏、失真现象严重,犹以人口和田土面积数据记载最为混乱,一直是困扰明史研究者的难题。正如林金树先生所言,“如果没有有助于说明问题的新资料出现,任何评估都难免游谈无根,很难得出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因此我们在引用此类数据时还应保持谨慎。
此外,本书对明代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诸问题的研究,多从“国家”视角、大时段、全局处着眼,使用考据方法和前沿理论对传统文献资料加以解读,尚缺乏对一村、一姓、一家、一户的个案研究和实地考察。由于作者的侧重点不同,这并不构成对著作本身的质疑,但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全貌来说,尚显缺憾。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华南、华北和江南等地一些学者正努力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欧美、日本同行的经验,“走向民间”,“走向历史现场”,在各地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关注于对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解读,形成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区域史专题成果。王家范先生认为,这种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内在复杂性,提供了前此少有人注意的视界与第一手材料”。因此,广泛汲取前人成果,合理把握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理论与实践,文献与田野等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明清农业社会经济史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