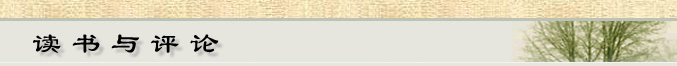对洛克“神学”政治思想的梳理——解读《政府论》上篇
亚洲文明研究院07级硕士研究生 常文相
约翰·洛克(1632——1704)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于1689年出版了他的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政府论两篇》,其基本精神在于对1688年刚结束的英国所谓“光荣革命”进行辩护和理论总结。“上篇着力于驳斥保皇派菲尔麦鼓吹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的反动论点,下篇则正面阐述洛克本人关于议会制度的政治理论”,([英]洛克:《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以下引用该书之处,仅注页码。)本文拟从上篇入手,着眼于洛克以自己的神学政治思想对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学说的批判,以期梳理出他的思想脉络,为进一步研究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建构打下基础。
一、批判的总论点
上篇一开始,洛克首先确立了他要批判的论点:“一切政府都是绝对君主制”,“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第2页)这个论点以罗伯特·菲尔麦爵士为代表,他在自己的《先祖论》一书中反复宣扬:“人类不是生而自由的,因此绝不能有选择他们的统治者或政府形式的自由;君主所有的权力是绝对的,而且是神授的,奴隶绝不能享有立约或同意的权利;从前亚当是一个专制君主,其后一切的君主也都是这样。”(第3页)针对于此,洛克高举起人类天赋自由的理性主义旗帜,以《圣经》为依据,开始了对菲尔麦的学说的批判。
二、模糊的前提
菲尔麦为了证明“人类不是天生自由的”,在学理上首先便把父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并加以强化,他认为“‘人们生来就是隶属于他们的父母的',因此,不能够自由。他把这种父母的威权叫做‘王权'、‘父权'或‘父亲身份的权利'”。(第4页)但是洛克指出,菲尔麦并没有明确阐释父亲身份或父亲的威权究竟是什么,而只是就谁有这个父权大发议论。洛克只得自己对散见于菲尔麦著作中的所谓父亲的威权的说明加以概括:“这种‘父亲的威权'或‘作为父亲的权力',照我们的作者的意思,就是一种神圣的、不可变更的主权,一个父亲或一个君主对于他的儿女或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据此享有绝对的、专断的、无限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从而他可以任意取得或转让他们的财产,出卖、阉割和使用他们的人身——因为他们原来全都是他的奴隶,他是一切的主人和所有者,他的无限的意志就是他们的法律。”(第8页)同时菲尔麦还认为,这种威权最初授予了亚当,“并在这个假设之上建立了君主的一切统治和一切权力”。(第8页)然而同样,菲尔麦仍然没有对作为建立君主专制政府的基础的亚当的主权给予充分论证,他只是在理所当然地反复强调,亚当有生杀予夺的绝对统治权。那么,论据的不充分反倒更证明了绝对君主制本就无道理可讲,这种学说除了“谄媚人们天生的虚荣心和野心”以及导致统治者为所欲为而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外,别无用处,更不用说能泯灭掉人类的天赋自由了。(第8~9页)
三、从神创得来的统治权的困境
菲尔麦君权神授学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是亚当由于为神所创造,他说:“如果不否认亚当为神所创造这一点,人类的天赋自由便是不可想象的。”(第12页)而洛克认为,亚当从上帝手中直接取得生命与人类的天赋自由并不矛盾,“单是神的创造这一点并不能给予他以统治权”。(第12页)因为,不光是亚当,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对此,菲尔麦又进一步说明:“亚当是基于上帝的选任而获得他的称号的。”(第12页)要是把他的“神创说”与“选任说”联系在一起,就成了:“亚当一创生,就由于上帝的选任而成为世界的君主,虽然他还没有臣民;因为,虽然在没有臣民以前,实际上不可能有政府,可是,基于自然的权利,亚当理应是他的后裔的统治者,尽管不是在事实上,但至少在外表上,亚当从他的创生时起就是一个君王。”(第13页)洛克把菲尔麦所说的“君主”当作“除了其余的人类以外的整个世界的所有者”,把“选任”当作“上帝对亚当的真实赐予和通过明白启示的授与”来理解,那么菲尔麦的论证方法,就存在两个明显的谬误:第一,《圣经》原文中,在夏娃没有被创造和交给亚当以前,上帝并没有对亚当实行授予。况且,菲尔麦把上帝要求夏娃对亚当的服从作为“政府的原始授予”,但是这件事发生时,距离亚当被创造已经很遥远了。所以,亚当不是一创生,就基于上帝的选任而成为世界的君主。第二,在逻辑上,菲尔麦把上帝授予亚当为世界的所有者的原因说成是:“基于自然的权利,亚当应当是他的后裔的统治者。”这个推理不通,既然上帝已经明白赐予了,那么就不应再需要基于自然权利的统治权,两者互相矛盾,不能把这个说法当成是上帝赐予的证据。(第13~14页)
由于菲尔麦用词混淆不清,使得对“君主”和“选任”的含义还有另外的解释,即把“上帝的选任”当成“自然法”,把“世界的君主”当成“人类的至高无上统治者”,但是这对于菲尔麦的论证没有帮助。(第14页)因为,就算承认一个人应是他的儿女们的天生的统治者,但是这个自然权利是以本人是他的儿女们的父亲为前提的,所以,亚当在还未做父亲之前,就没有充当统治者的自然权利,在遵循自然法则的意义上,亚当仍然不能一创生就成为君主。(第14~15页)尽管菲尔麦给自己找了台阶下,辩称亚当是“外表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正是因为亚当没有实际享有统治者的权限,那么他在创生时也就根本没有这个权限。(第15页)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他既有生育儿女的可能,他就有做统治者的可能,因此他获得统治那些从此繁殖出来的儿女们的自然的权利——不管这权利是指什么。”(第16页)
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上帝的意志还是自然的权利,亚当都不能一创生就成为世界的君主而享有主权,既然这样,那么人类的天赋自由便有成为合理的可能。这一章,洛克虽然总体批判了亚当由于为神所创造而享有主权,但实际上对菲尔麦从《圣经》里得来的其他论点都有所涉及。在下面的几章中,洛克就《圣经》论《圣经》,对菲尔麦的学说展开了更为具体细致的考察与批判。
四、对全人类的赐予
亚当既然不能因为其为神所创造而成为天生的统治者,菲尔麦接着又抛出了证明亚当有统治权的另一个论据,即“亚当基于上帝的赐予而成为万物的共同主人”。(第18页)《圣经》中是这样说的:“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育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各样在地上走动的生物。”(第19页)菲尔麦由此下结论道:“亚当既取得对一切生物的统治权,因此他就成为全世界的君主。”(第19页)但是,这里“统治权”的含义可以从两个层面解释:一个是“给予了亚当以对大地和一切低级的或无理性的生物以所有权”,另一个是“给予了他以包括他的儿女在内的对一切地上生物的支配和统治的权力”。(第19页)从《圣经》上看,显然上帝“许给亚当的只是所有权”,“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亚当的‘君权'”。(第19页)这里,菲尔麦又含糊了词义,混淆了视听。基于此,洛克提出了两点反对意见:“第一,根据这个赐予,上帝并没有给予亚当以对人类、对他的儿女、对他自己同类任何直接的权力,因此,他并没有基于这种特许而成为统治者或‘君主'。第二,基于这个赐予,上帝给予他的不是他对低级生物的‘个人统治权',而是与一切人类相同的权利,所以他也不能由于这里给予他的所有权而成为‘君主'。”(第19~20页)关于第一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所指是明确的了,对于“地上走动的生物”,在《圣经》里被分为三类:牲畜、野兽和爬行动物,而且在用词上“生物”对应“兽”、“走动”对应“爬行动物”。(第20页)至此,上帝已经创造出了世上的非理性动物,这些动物将按照预定的设计,置于人类的统治权之下,但是在这些话中,“实在没有一点痕迹,可以拿来牵强附会地表示上帝给予一个人以统治别人之权,亚当统治他的后裔之权”。(第21页)也就是说,“地上走动的生物”不是指人类,“人类是不能够包括在这个赐予之中的,亚当也并没有被给与统治他自己同族的任何权力”。(第22页)关于第二条,“不管上帝在这个赐予的话中所给与的是什么,他却不是把其他人排除在外单独地许给亚当,因此,无论亚当由此取得了什么样的统治权,它都不是一种个人统治权,而是一种和其余的人类共有的统治权”。(第23页)这已从《圣经》原文的字句中明确地显示出来,“因为这个赐予是用复数来表示的——上帝祝福‘他们'并对‘他们'说享有统治权”。(第24页)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字样必然包括全体人类,一切个人都接受上帝的赐予。综上两点,洛克认为,既然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和外貌创造了人类这一有智力且有能力行使统治权的生物,那么作为体现上帝形象的智力禀赋就应属于全人类所有,因而全人类都有能力享有对低级动物的统治权。
同样,菲尔麦为要维持亚当的所有权和个人统治权,在《圣经》中接下来的类似地方又想要推翻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的共同赐予。首先,他强调,“纵然在祝福时儿子们和挪亚一道被提及,但是最好解释为含有从属的意思,或解释为继承的祝福”。(第26页)洛克表示,这直接违背了《圣经》明文,只是菲尔麦为适合自己的主张而作的主观臆断。上帝在祝福时明确说道:“尔们要生育众多,布满大地。”(第27页)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儿子凡事都须经父亲的许可,以对父亲的从属来继承上帝的祝福,那是不会达到上帝使世界人类繁衍的愿望的。另外,在祝词中上帝还说到:“我使一切的兽类都惊恐和畏惧你们。”(第28页)这是不是得认为:“没有得到挪亚的许可或非等到他死后,兽类只畏惧挪亚一个人而不畏惧他的子孙呢?”(第28页)要是按菲尔麦的逻辑,只能推导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因此,把上帝在洪水之后给予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的祝福同创世后给予亚当的祝福互相参照,既然“挪亚享有亚当在洪水以前享有的同样称号、同样所有权和统治权是可能的”,与此同时挪亚与他的儿子们在对上帝的赐予的享有上是广泛而平等的,那么就只能使洛克更加断定,《圣经》中上帝没有赐予亚当以任何个人统治权。(第29页)其次,菲尔麦又退一步暗示挪亚对万物的所有权缩小了,他说上帝对亚当与挪亚的赐予是很有差别的,“第一次祝福给予亚当以一种对地上世界和一切生物的统治权,第二次祝福则允许挪亚享有利用生物作为食物的自由”。(第30页)或者说,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并没有给予他们以统治权或所有权,而只是扩大了食粮的范围”。(第30页)然而洛克认为,“上帝说的‘我使一切兽类都必惊恐和畏惧你们'一语就表示了统治权,或者,人类对其他生物的极大优越地位被确定了的意思”,但是这仅限于人类对低级动物的权力。(第31页)而且,“很明显的,在这一次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的祝福中,所有权不但是用明白的文字给与的,而且其范围比给予亚当的还大”,因为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我把它们都交付你们的手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第31页)洛克认为,这里食粮范围的扩大正代表了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对动物的所有权的扩大,因为在此之前,“对于野兽,亚当也确乎没有绝对的统治权”,而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却得到了亚当不曾有的对生物的所有权,即在上帝允许下的“利用它们的自由”。(第32页)正因为人类利用动物的自由要经过上帝的授予和允许,所以洛克总结:“从上述的一切,我认为很显然亚当和挪亚都不享有任何‘个人统治权',也不享有任何不包括他的后裔在内的对生物的所有权,只是当他们相继增长而需要它们并能够利用它们时,他们才享有这种权利。”(第32页)
洛克从菲尔麦所引的《圣经》文字中“看不到有倾向于‘亚当的君权或个人统治权'的任何东西,而是恰恰与此相反”,“这段经文不但远远不能证明亚当是惟一的所有者,正好相反它证实了一切东西最初都是人类共有的”,因此,“建立在个人统治权之上的亚当的主权,既然没有支持它的任何基础,必然是站不住脚的”。(第33页)
五、男女之间
菲尔麦用以作为亚当享有君权的另一处依据,为《圣经》中上帝对夏娃说的话:“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第36页)菲尔麦说:“这就是政府的最初授与。”(第36页)洛克回应,如果考察经文,想想上帝在这里对亚当和夏娃说话的场合,“考虑一下他正是对他们俩违反意志的行为宣布判词和表示愤怒,我们就不能假想上帝是在这个时候给与亚当以特权和特许,授与他以尊严和威权,提高他到享有统治权和君主权的地位”。(第36页)亚当在原罪的堕落中也同样有份,同样是被上帝贬低了的,那么,“很难想象上帝竟会在同一个时候使他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君主,又是终身的劳动者。把他赶出乐园去‘耕种土地',而同时又赐给他以王位和属于绝对权威的一切特权与舒适生活”。(第37页)同时,洛克还认为,菲尔麦称之为“政府的最初的授与”的这些话,“并不是对亚当说的,那些话里面的确也不曾许给亚当任何授与,而只是对夏娃的一种责罚”。(第38页)《圣经》原文是这样的:“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第38页)据洛克看,“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并没有给予亚当以对夏娃的威权,也没有给予男子以对其妻的威权,而只是预言女人可能遭受的命运”,如果一定要把其理解为上帝给予亚当以任何权力的话,“它只能是一种婚姻上的权力,而不能是政治权力——在家庭中丈夫作为财物和土地的所有者而具有的处理有关私人事务的权力,以及在一切有关他们的共同的事务上,丈夫的意志优于他的妻子的意志;但不是对妻子有生杀之权的政治权力,对其他的人就更谈不到了”。(第39页)
总之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上帝对夏娃说的话当作是一种政府的最初授予和君权的基础,否则,世界上有多少丈夫就该出现多少君主了。
六、父亲身份的权力
以上,洛克已经把菲尔麦据以证明亚当的主权的两处《圣经》原文都考察过了,“其实这两处原文的一处,是只指低级动物对人类的隶属,另一处则指妻子对丈夫应有的从属,这两个地方比起政治社会中臣民对于统治者的从属来,都相差甚远”。(第41页)事实上,菲尔麦论证亚当无论是由神所创造并赐予权力,还是取得夏娃的从属而享有主权,其落脚点都在于其每时每刻不在反复强调的由“父亲的身份”而来的专制君主制度。也就是:“上帝自己已把‘最高权力'授与和建立在父亲的身份上,规定了这种权力为君权,并将其赐给了亚当本人和他的继承人。”(第41页)由此,菲尔麦的学说开始了从君权神授向王位世袭的过渡。与此同时,洛克也针锋相对,向亚当由于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的论点发起了批判。
菲尔麦主张,“不光是亚当,连以后的先祖们,基于父亲身份的权利具有对他们的儿女的主权”,同时,“这种儿女的服从是一切君权的渊源”。(第42页)洛克自然也承认,“生育使父母获得对子女的权力”,但是他认为这个权力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全然不是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第42~43页)接着,洛克列举了用来证明父亲因生育儿女而获得对他们的绝对权力的论证。其中之一为:“儿女的生命和存在是从父亲来的,所以父亲享有对于他们的儿女的生命的权利。”(第43页)对此,洛克回复:“首先,凡是给别人东西的人不一定因此就总有取回这东西的权利”;第二,只有上帝才是“生命的创造者和授与者”,赋予人类生命与意识,并“以他的无限智慧,把强烈的性交欲望安置到人类的体质之中,以此来绵延人的族类”,所以,人间的父母都不能以是其儿女的创造者自居。(第44~45页)然而菲尔麦却另有一种想法:“我们知道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就给了男人以对女人的主权,因为男人在生育中是较高贵的和主要的参与者。”(第46页)但是洛克指出,《圣经》上从未提到过这样的话,而有的只是“生他的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第46页)证明父亲对其儿女具有绝对权力的另一处论证为:“有些人认为人类‘遗弃或售卖'自己儿女的实践是他们对儿女的权力的证明。”(第46页)洛克断言,“他们只是把人性可能作出的最可耻的行动和最伤天害理的谋杀拿出来作为他们的意见的根据”,完全违背了上帝的训诫及自然的理性。(第46~47页)“如果曾经出现过的事例,都可以当成是理应如此的通则”,那么,历史上秘鲁的印卡人吃掉“自己跟从战争中俘来的女人所生的儿女”的酷嗜,就更是表现绝对父权的最完美的例证了。(第47页)
菲尔麦为要证实父亲的这种天赋威权,又从《圣经》里上帝的明白训诫中拿出来一个蹩脚论证:“我们看到在十诫中上帝用‘孝敬你的父亲'一语来教人服从长上,这样,不独是政府的权威和权利,而且连统治权的形式和享有这个权力的人,全是上帝的规定了。最初的父亲所享有的不仅是单纯的权力,而且是君主的权力,因为他是直接来自上帝的父亲”。(第49页)然而菲尔麦歪曲了上帝的训诫,把“‘和母亲'三字视作不足为凭的经文而经常把它们删去”。(第49页)洛克举出了一大堆文献证明:“《圣经全书》既常把父亲和母亲连在一起,我们因此可以断言他们从自己的儿女那里应受到的孝敬,是一种平等的、属于他们两人的共同权利,既不能由一人完全独占,也不能有一个人被排除。”(第51页)洛克认为,“享有这种‘孝敬'的资格是由自然赋与父母的,是一种基于他们曾生育儿女而归他们享有的权利”,“母亲既然享有她的儿女的孝敬的权利,而不受她的丈夫的意志的约束,因此,我们看到‘父亲的绝对君权'既不能以此作为根据,也不能与此相容”。(第52页)要是按照菲尔麦的观点推论下去,如果“父亲由于对于他的儿女享有绝对管辖权,因而对于他们所生的,也享有同样的权力”,那么,“祖父基于他的主权,能否取消他的孙子根据第五诫对于他的父亲应尽的孝敬”,这依照常识显然不能。(第52~53页)所以,孝敬父母是“纯然关于父母和儿女间的关系,其中绝不含有统治者的权力,也不从属于它”。(第53页)如果把父亲的威权理解为政治上的隶属或服从而施行于全社会,那么只会给社会带来祸乱。一方面,父亲的身份要是代表统治者至高无上的主权,就意味着“他的臣民即使是父亲,也不能享有对于他们的儿女的权力,不能享有受他们孝敬的权利”,“因为这种享有臣民服从的权利已被全部赋与别人了”;另一方面,既然每一个孩子对他的父亲应尽的义务都是其必然享有的政治支配权,“这样一来,有多少父亲,就会有多少统治者”;此外,若是母亲也享有这种权力,就更加“破坏了单一的最高君主的统治权”。(第53~54页)
除了自然权利的丧失外,我们再从统治权被分裂的角度来看待把父权作为绝对和惟一的支配权的谬误。照菲尔麦的计算法,“亚当的父亲身份所享有的无限和不可分割的统治权,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只存在于第一代”,当他一旦有了孙儿,便说不通了。(第57页)因为,“亚当作为他的儿子们的父亲,‘对于他们拥有绝对无限的王权',由此,对于他们所生的,以至世世代代都有支配权,可是他的儿子们——即该隐和塞特——同时对于他们的儿女也享有父权,因此,他们同时既是‘绝对的主'又是‘臣下'和‘奴隶',亚当作为‘他一族的祖父'拥有一切权力,然而他的儿子们作为父亲也有一份权力”。(第57页)尽管菲尔麦限定亚当的儿子们“仍须从属于最初的父母亲”,但是这种区分无甚意义,因为父亲对其儿女应有的自然的父权,本就不能作为亚当绝对权力的从属从他那里受委托而来。(第57页)菲尔麦一面承认父子之间的自然的权力,一面又断定这种权力是绝对无限的,他让一种绝对无限的权力去从属于另一种同样绝对无限的权力,就好比“在同一政府中,同时既是奴隶,又是绝对的君主”一样,矛盾到无以复加。(第58~59页)把父权绝对化以后导致王权的享有步入了极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必然会出现:“或是亚当的儿子们在亚当在世时就和其他父亲们一样……‘根据父亲身份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儿子们享有王的权力';或是‘亚当根据父亲身份的权利并不享有王的权力'”。(第59~60页)非此即彼,如果给予父权以王权,那么仍然是有多少个父亲就有多少个君主;如果不给予父权以王权,那么就不存在对父亲的主权与最高地位的绝对服从,菲尔麦的全部政治学便立刻寿终正寝了。总之,因“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除了把世界上一切合法的政府推翻、摧毁,并代之以动乱、专制和篡夺以外,是没有任何别的用处的”。(第61页)
七、上帝的意图:基于同意建立政府
在洛克看来,上帝不可能“给予一个人以支配别人人身的至高无上的专断权”,甚至那个人“对于那些不承认他的主权、不服从他的意志的其余人类,可以随心所愿地不给他们食物,而让他们饿死”。(第33~34页)反而这种想法倒更要合理一些:“既然上帝吩咐人类生育繁衍,他自己就应该给予全体人类以一种利用食物、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权利——这些东西的原料上帝已为他们作了那样丰富的供应——而不应该使他们的生存从属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具有随意毁灭他们全体的权力”。(第34页)进一步说,“作为一切人类之主和父亲的上帝,没有给予他的任何一个儿女以对世界上的特定一部分东西的这种所有权,倒是给予了他的贫困的兄弟以享受他的剩余财物的权利”,所以,“一个人不能够基于对土地的所有权或财产权而取得对别人生命的正当权力”,而只有契约才可以“给人以支配别人人身的权力”。(第34~35页)在这里,洛克把财产权与人身自由权分别开来,指出穷人人身的自由与否并不从属于富人财产的多寡,主人的所有权只是“起源于穷人在宁愿做主人的臣仆而不想挨饿的情况下所表示的同意”。(第35页)主仆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主人对仆人“只能在不超过他在契约中所同意的限度内对他拥有权力”。(第35页)于是,洛克眼中的主权和所有权的基础,在于“只要任何东西,能因满足别人保全其生命或保全他视为珍贵之物的需要而成为一个条件,使他不惜以其自由作为代价来进行交换”。(第35页)由此,政府的建立便不是出于上帝给予个人以统治权力,而是“由那些运用自己的理性结合成社会的人们通过计议和同意而组成”的。(第4页)
八、关于理性
关于理性,洛克这样描述道:“理性把一个人提高到差不多与天使相等的地位,当一个人抛开了他的理性时,他的杂乱的心灵可以使他堕落到比野兽还要远为残暴。人类的思想比恒河的沙还多,比海洋还要宽阔,假使没有理性这个在航行中指示方向的惟一的星辰和罗盘来引导,幻想和情感定会将他带入许许多多奇怪的路途。想象总是不停地活动着,产生出形形色色的思想来,当理性被抛到一边时,人的意志便随时可以做出种种无法无天的事情来。” (第48页)他接着又对非理性的宗教、政府和习俗的起源做了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最走极端的人就会被众人视为最适宜于领导的人,并且一定会得到最多的附随者。由愚昧或狡黠开始的事情一旦成了风尚,习惯就使它神圣化,违背或怀疑它,就要被人目为大胆或疯狂。一个以公平无私的态度来考察世事的人,将会看出世界上一些国家中有那么多的宗教、政府和习俗就是以这种方式成立和继续下来的,因此他也就不会对于盛行在人世间的这些习俗予以重视,倒是有理由认为那些因顺从自然而生存得很好的非理性的和没有教养的栖居者所在的山林,比起那些在他人的榜样影响之下逾越常轨而自称文明和有理性的人们所居住的都市和宫殿来,更适合于作为我们行为与生活的典范。”(第48页)
洛克批判菲尔麦学说的两大法宝,一是《圣经》,即上帝的意志;一是理性,即人类的自然权利。在他看来,上帝的意志是要保护人类的自然权利的,也就是“要求在高度完善的情况下使人类滋生和种族繁衍”。(第49页)所以,《圣经》的启示与人类的自然权利不但不矛盾,反而是推进人类天赋自由、遏制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有意思的是,菲尔麦恰恰也自称是以《圣经》和理性为依据来标榜其学说的,只是与洛克不同的是,他认为人类天生不自由,上帝从一开始就是要把人类变成君主的奴隶。这样,与其说是两人围绕《圣经》展开了论战,倒不如说是更突显了两种人性的交锋。两人在保有对上帝信仰的同时,也都拿上帝当作了关注现实的工具。
九、回到第一章:错在哪里?
到此为止,洛克已经把菲尔麦提出的“亚当有‘绝对无限的统治权',因此,人类从来都是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绝没有任何自由的权利”的假设,全部考察了。(第55页)要是我们认可洛克的看法,即“如果上帝的创造,只给予了人类以一种存在,而不是把亚当‘造成'‘他的后裔的君主';如果亚当不是被确立为人类的主人,也没有被赋与一种除了对他的儿女外的‘个人的支配权',而只是被给予了凡是人类子孙都共同享有的支配土地和下级动物的权利和权力;如果上帝也没有给予亚当以支配他的妻子和儿女的政治权力,而只是作为一种惩罚,使夏娃服从于亚当,或者只是在有关家庭共同事务的处理上对女性的从属地位作了预言,但不曾因此而给予作为丈夫的亚当以必然属于行政官长的生杀予夺之权;如果父亲们不能因生育儿女而取得对他们的这样的支配权;如果‘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一诫命也没有授与这种权力,而只是责成人子对双亲同样地应尽责任,不论他们是否臣民都是一样,并且对母亲也与对父亲一样”。(第55~56页)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人类确实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由'。这是因为一切具有同样的共同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从本性上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该享受共同的权利和特权。”(第56页)这样,让我们再回到第一章菲尔麦的总论点,洛克其实用与菲尔麦同样的依据——《圣经》,而从根源处就把菲尔麦的神授的绝对君主制与人类天生不自由等学说彻底否定掉了。菲尔麦以后的论证就好比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用他自己说别人的话说:“最初的谬误原则一旦失败,这个绝对权力和专制制度的庞大机构也就随之坍塌了。”(第56页)
人性的解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如今,追求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已成为世界人民的良好愿望,全人类都在为其最终的实现而不懈努力。倘使菲尔麦活到今天,恐怕也将不得不对人类的天赋自由予以承认。这一点暂且不谈,我们只对菲尔麦的学理逻辑加以考察,会发现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或许就是把父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并加以极端绝对化,因而,对于两者自然的权利和上帝的意志之间隐含的矛盾,在解释时便失去了弹性。其实菲尔麦倒是可以把亚当享有主权完全归结于上帝的意志,然而《圣经》里还没有这样明确的启示;于是,他只得又把王权的来源依据到父亲的身份上,但是既然父权等同于绝对无限的王权,那么,父亲对于其儿女的意义在自然权利的层面上又解释不通了。菲尔麦的理论,基干既已摇摇欲坠,枝叶就极易被层层剥离,洛克正是抓准了这个致命弱点,最终将其批判得体无完肤。
十、小结
菲尔麦的主张亚当的主权和反对天赋自由等观点,散见于他的众多著作中,洛克找出了其中最成体系的论证,即是:“如果上帝只创造了亚当,并从他身上分出一块骨肉来造成女人,如果一切人类都是作为他们的一部分从他们俩生殖繁衍下来,如果上帝还给予亚当以不仅对这个女人和他们两人所生的儿女的统治权,而且还让他去征服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生物,这样,只要亚当生存一天,除非得到他的赐予、让与或许可,便没有人可以要求或享有任何东西。”(第11页)菲尔麦所依据的当然是《圣经》,他把自己强烈的主观意愿灌注到《圣经》故事中,期待《圣经》以君主专制的终极理论化身的形态展现于世人面前,使得人们信奉《圣经》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可了他的理论。菲尔麦这种凭借传统经典为自己的学说张目的做法,既是其获取自信与力量途径,也是世人们普遍易于接受的方式。因此,洛克要想彻底推翻菲尔麦的理论,也必须有效利用好《圣经》这一强大利器。其实两人无论是谁,都是在以自己的意图来揣摩上帝的意图,把自己的观点借上帝之口给表达出来,以实现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理论构建。只是,菲尔麦强调权威,上帝就被强化成掌管生杀予夺大权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服从即是死路一条;洛克则崇尚自由,他所描绘出的上帝更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慈祥老者,关爱着他的子民,造福于人间。
在对洛克的神学政治思想的梳理中我们发现,同样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圣经》教义的阐发,洛克却得出了与菲尔麦截然相反的结论,两人可谓同途殊归。洛克承认亚当为神所创造,承认夏娃对亚当的一般意义上的从属,承认亚当的父亲身份,但亚当并不因此享有主权;承认上帝的赐予,但这只是上帝对全人类的赐予,亚当仍然不能因此享有主权;既然连亚当都不享有主权,那么现世的君主就更没有资格拥有与行使绝对权力了。在菲尔麦论证中的根据与结论之间的关结点,洛克都一一重新做了细致阐述。两相比较,菲尔麦的论证造势虽猛,却外强中干,只是空喊口号,缺乏内在基础,终不免声亏力竭;而洛克的思想体系则更为严整缜密,破题有力,立题有理,在当时理性之风盛行于全社会的大背景下,更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意义。
菲尔麦原本的想法,是先依据《圣经》论证亚当拥有绝对权力,即是所谓君权神授;然后依据自然的权利论证亚当的嗣子承袭了他的王权,即是所谓王位世袭;最后把现世君主的权力与亚当的主权联系起来,从而为君主专制制度找到了合法性。然而,菲尔麦憧憬的上帝——亚当——嗣子——现世君主这个美妙的权力链条,在各个环节都被洛克给砸得粉碎。上帝是万能的主,但从上帝到现世君主之间,绝对权力断无可通达之理。因此,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合理的存在,权力与政府应该像洛克以上帝的名义所宣称的那样,是基于人们的同意而建立的。
洛克的《政府论》上篇,虽然语言冗长,思想跳跃,读来艰深晦涩,但经过仔细分析,还是能够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研究洛克的政治思想,首先梳理出他在神学意义上的对政治的看法,应该是一条正确的入门路径。尽管洛克的这种思想是以批判他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理论看似针对性大于系统性,但是他的一些主要的政治观点,如财产权、有限权力以及基于同意建立政府等等,在其批判菲尔麦的学说时都有体现,而这些政治观点将会在下篇中被具体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