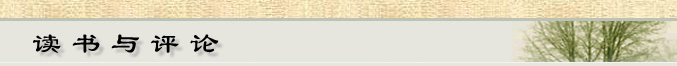2006年年末消息传来,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授予了著名华人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先生。“克鲁格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其旨在弥补“诺贝尔奖”在人文领域内的不足,而奖励那些在历史、哲学、 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研究、语言学、以及艺术与文学批评等学科领域内作出重大和深远贡献且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学者。此次获奖对于海内人望的余英时先生来说可谓实至名归,但更重要的不仅是对他个人数十年思考、笔耕的奖掖,还是对“汉学”和华语学术研究的认可,故而获奖一经公布,国内学界、媒体争相发表报道、评论。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余先生只是淡然地表示“希望这件事快点过去”。“青山原不动,白云自去来”,其实余先生作品在大陆的接受并不是平川坦途。由于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他与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相左,对其作品的系统性介绍还只是近几年来的事(主要包括三联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各自成建制出版的余英时文集,但是文集中的篇目都是经过了再编辑的选择)。而在这之前余英时先生的盛誉在大陆主要是建立在他的两本现已成为经典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198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基础之上的,其中后者在大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有着尤为突出的影响。(据他的学生在《南方周末》上的回忆文章,早在八十年代初这本书就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在国内知识界流传起来)这本《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以其深邃的学术视野(从先秦—秦汉纵贯至晚清—五四),新颖的学术方法(对中西史学、哲学、文学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独到的学术观点(如对中国文化中“反智”现象的辨析、对“现代”与“中国的现代”问题的梳理)给思想禁锢刚刚打破、亟待新风吹沐的大陆学坛带来了宝贵的思想和方法资源。毫不夸张地说它在中国二十世纪后期的再启蒙运动中是有一席之地的。笔者作为一个青年学人,对余先生和他的《中国思想的现代诠释》都是极为钦佩的,所以在此不揣冒昧简单谈谈个人的一点读书心得。
此书启发我的首先是其体现在结构上的思想。在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中“新批评”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形式即内容”,也就是说在这里“形式”不再像一个被动的、客体化了的容器安静地等在那里被各式生命的活水粗暴地填满、注入各种“内容”,而是主动地对其中的“内容”提出要求,并作为主体来塑造其中的“内容”与之共同指向“意义”。于是人们欣赏的不再只是碗里的水,而是精美的造型艺术玻璃器皿中液体晶莹的律动。通观《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目录,其结构不免令人迷惑。前边六篇以“先秦—秦汉”为中心,泛言中国文化多个层面。其后五篇以“明清”为核心,三篇言明清思想史问题,另两篇竟是对一部文学作品:小说《红楼梦》的研究。最后的压卷之作是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乍看之下这样的结构似乎失之于散漫,不象专题性的大块文章那样紧凑,而让人有思想难于凭附之感。其实个中正隐含着余英时先生的“微言大义”!我们说余先生学术思想深广且卓尔不群正是因为他能将中国传统有效地与西方学术思想进行缝合,在互相烛照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余英时先生早年对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借鉴。(见《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篇目)而在本书的结构里则明显凸现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这一著名历史哲学理论。雅氏在其卓越的历史哲学专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时性和不平衡性出发指出“公元前800—200年是人类精神文化产生突破的时期,在中国产生了儒、道、法、墨等各家哲学。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则有了锁罗亚斯德教、在古代希腊产生了像荷马及苏格拉底式的人物……这一时期为其后人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他将历史发展中这样的关键时刻定义为“轴心时代”,并指出各个历史时期并非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是有着各自的“轴心”。从这一理论反观余英时先生对其作品的构建,我们不难发现他正是抓住了这些历史“关键时刻”( 作为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一个是以铁器为物质基础,以诸子哲学为精神成果的“先秦—秦汉”;一个是以工业文明为物质基础,以新文化运动为精神成果的“晚清—五四”)来切入中国文化的肌体,发现其中的病灶所在,并“引发疗救的希望”(鲁迅语)。这正是大师把握历史、理解历史的手眼!仅仅借用西人理论套用在自己身上,不过是拾人牙慧,余先生更精彩的是对在此基础上对自身传统的独到理解,从而在真正意义上作到了融会中西,而不是简单的拉郎配。例如,雅斯贝尔斯指出了“古典时代”(即上文所引对公元前800—200的论述)这一轴心期逐渐走向瓦解的原因是其后帝国的建立和帝国对思想的统一所造成的禁锢,而对于各帝国统一、禁锢的具体机制则语焉未详。余英时先生通过对《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篇中对此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后:指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实际已经被歪曲而丧失活力,其旨仅限于保守的经学研究。法家作为王朝的实际思想纲领着力打击异端。而道家则成为知识人(仕)的鸦片和帝国体制中的润滑剂。于是“三道”圆融共同造成了“反智”(反智识主义,西文作anti-intellectual)的事实。表面是“万班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骨子里却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批判何其精彩、又何其具有现实意义!这才是最中国的,也是最世界的。
余英时先生作品的又一魅力在于其学术方法上对哲学、文学观念的借助。这突出表现在书中两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里。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余先生借用了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 · 库恩在《必要的张力》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和使用的“范式”(paradigm)理论,从而将纷繁复杂的红学研究成果条理清晰地整合起来。库恩本是用这一理论来描述并解释经典物理的建立和动摇的过程,他指出学科科学研究是不同“范式”相互取代的过程,某一“范式”规定了当下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内容,并形成了以此为中心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处于基本稳定的常态,直到这一“范式”在学科研究中不再有效、遭遇危机,并受到其他另一种的“范式”的挑战,最终被新“范式”所取代而重新达到稳定的常态研究。在此基础上,余英时先生把近代以来的红学研究纳入了几个不同的“范式”:第一,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引派”。这一派的核心“范式”是追求对《红楼梦》进行政治解读,指出小说是为了宣扬民族主义、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的;第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该派的核心“范式”是认为《红楼梦》是作家本人的自叙传,寻找曹雪芹身世与小说内容的对应。第三,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派”。其核心“范式”是中共官方政治思想在学术界的延续,认为小说表现的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 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第311页)这样一来近代原本芜杂的红学发展史在科学理论的关照之下纲举目张。以什么形式来书写思想史可谓当代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复旦大学学者骆玉明、章培恒从“美”和“人性”的角度出发重写文学史到世纪之交葛兆光从“普遍思想”的角度出发重写思想史,我们不能不说余英时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尝试是开风气之先的。今日学人往往大谈特谈跨学科研究,又有几人能真正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历史呢!最可贵的是余先生还在归纳总结了前人思路之后对于红学发展新维度进行的开拓“新范式是把红学研究的中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联系上……新范式的两个特点是:第一,它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因此特别重视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和虚构性。……第二,新范式认定小说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隐藏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之中,尤其强调二者之间的有机性”,余英时先生将小说的内在结构概括为“两个世界”,“红楼梦主要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这个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上……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中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世间的最大的悲剧。”(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356页)历史的主体是人,而又有多少历史著作有着像余先生作品这样深厚的人文关怀呢!余先生对《红楼梦》的解读充分表达了一个史学家的诗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文学比历史更接近真理,文学更富有哲理”这是说历史往往停留在庸俗的事实层面而缺少终极关怀。但是了不起的史学作品却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关怀,鲁迅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离骚》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浪漫抒情文学的滥觞。将历史的兴变与人生的感喟相结合,让史学在求真的基础上焕发出人性的光彩,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做到了这一点。
最后,我想对余英时先生在本书中所体现的自由主义观点谈谈个人的看法。我们应看到余英时的自由 主义是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关于偏向于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界定见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种选择》一文,孟繁华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上卷)。陶东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困境是:保守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相互勾连,为了维护传统文化而不惜背离自由的目的,而自由主义则常常走向狂躁的激进主义与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使中国文化面临深刻的断裂,而且最终同样背离了自由的宗旨。二者的持续紧张与消长是贯穿20世纪中国始终的主线。正如贝尔称自己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余英时在文化上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是 一种英国式的、经验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而不是法国式的、狂飙突进式的自由主义。这一点从他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在这本书的压卷之作《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里,余英时着力为“五四运动”寻找中国本土的传统资源;在 其另一部广有影响的著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甚至还为资本主义发生在中国找寻本土理论的支撑。尽管其论述是有着深厚思想理论依据,但还是难免让人想到鲁迅先生所批判过的“我们祖上是阔得很的”。历史地客观来看“五四运动”其实是断裂大于继承、绳祖不敌革新,无论是胡适先生所推动的白话文运动受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启发,还是鲁迅先生所创作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果戈理的借鉴,以及陈独秀所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西方背景,都从事实上证明了“五四”属性。我无意臧否余英时先生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而是深切地看到了当一个历史的审视者纠缠于历史之中而成为一个历史行为人时艰难的步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从这个角度来说余英时的困顿也正体现了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