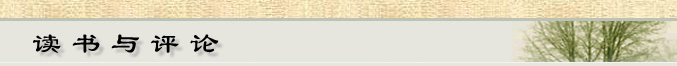人类历史的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此话虽然不乏夸大其辞,但也足以表明美国,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舞台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而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及地位的 “ 显性 ” 体现即为外交,由此国内对美国外交的研究热便兴盛了起来,但无论针对某一个体案例分析还是具有时空跨度的政策概述似乎总也逃离不出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的视野,“ 这些方面无疑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要素,也最能直接反映出主权国家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追求的利益 ” 。(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以下引用该书之处,仅注页码。)但这些因素具有宏观性、时段性且是变化着的。而 王晓德 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可谓是独辟蹊径,他从文化这一深层的、内在的、稳定的、微观且更具历史积淀性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及某些外交现象进行透析。虽然此前国内一些学者针对文化与外交关系方面也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文,但却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问世,而 王晓德 教授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的推出为此方面的研究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他从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来剖析美国外交,“由内向外” 地看历史。拜读完这本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我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美国文化与外交》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优点即为:它为中国学术界对于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 从美国文化着手研究外交,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
无疑地,当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成为民族国家并参与到了国际事务中时,它对外则代表了整个国家利益。而在对外事务中,为了维护政治、经济、安全等国家利益时,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外交政策,并与其他国家发生着外交关系。但不论这种外交政策的出台是由于经济利益、国际政治,亦或涉交国、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它总是逃脱不了整个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制约。特别是在全球化步伐日趋加快的今天,“文化日趋成为社区以及地区,国家与国际事务中的越来越有影响的力量
。”(第2页)更何况,文化利益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和发展则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体系,这就要求在世界一体化的强大融合流中尽可能的争取本国的文化利益。从表面上看,历史舞台是为精英人物准备的,自然他们的 “举手投足” 便成了世界的焦点。但要知道,这些精英人物也是生长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的,所以他们的“举
止” 间都“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中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现出来,给本国的对外政策打上明显区别于他国的烙印。”(第3页)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如同一个模子一样塑造着这个国家人民的特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由此便出现了“美国造”、“中国造”、“日本造”诸如此类的词语,这种塑造是超脱于“个体的生命和具体的历史时代”的内在的文化心理,它是经过代代传承而又传承代代的文化意识,它具有相对稳定的状态。文化的这种稳定性说明它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不但塑造了它的人民,并透过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反映到了国家的内部政策制度和外部事务中。而这部分精英人物之所以成为精英正是由于他们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该书以希特勒为例从反面论述了这一观点。作者认为,虽然希特勒扭曲了德国的整体利益,使之成为其追求私利的掩饰,但仍能被德国的国民所接受,要不然他也不会成为二战的始作俑者,而原因恰恰在于“所扭曲的利益并不与国家的文化精神相悖逆。
”(第6页)可见,无论顺应还是扭曲了整体利益,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外交政策总也摆脱不了该国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文化底蕴对一个国家的外交起着潜在的制约作用。
既然如此,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外部的关系时,文化因素便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有形或无形的作用,给美国对外关系打上了带有明显的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天定命运”的使命观、“上帝的选民”的种族优越主义、讲求功利的务实精神以及在此思想推动下的所谓“输出民主”、“人权外交”的扩张意识、“理想主义”的外交迷惑,无一不根植于美国文化之中。但这些文化价值观在美国处理具体外交事务的时候变成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成为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借口,这使得美国外交政策往往体现出表里不一。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如果说过去美国文化在外交中主要发挥一种潜在作用的话,那么,现在却被美国政府决策者有意识地作为实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筹码。”(第13页)
多层次多方位地阐述美国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是该书的另一大特色。作者在做这方面的论述时紧紧抓住美国文化中最为原始也是最为本质的核心——“使命观”来加以阐释。
书的开篇第一章便直接切入了这种“使命观”,足以显示它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及今后对美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主体文化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而“使命观”正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反映。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则是早期移民潮中的主流,他们携带着新教伦理来到了这片广袤无垠的“希望之乡”。由于强烈的宗教信念,使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派往人间来救赎世人的,身上肩负着“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责任和义务。”(第20页)但因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就必须通过在尘世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 “选民” 身份和神圣的使命。而北美大陆的实际地理环境似乎又为这种思想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说辞: “ 背后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头顶是茫茫天际的上苍,前面是孤寂可怕的荒野”。(第25页)这样的绝境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身负的特殊“使命”: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片荒野之地改造为文明的故土,使之成为万世瞩目的 “ 山巅之城 ” ,这样的“理想王国”应该受到全世界的敬仰和效仿。这种思想从北美早期移民中传承下来,成为美国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 ——“使命观”。即,美国人是被上帝选定的,美国作为一个受到上帝恩宠的国家是世界的楷模,自身肩负着拯救世界和全人类的神圣使命。“使命观”作为美国文化中最本质核心的内容贯穿于美国的历史之中,并对美国对外关系中诸多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作者分别就长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扩张主义”、“种族主义”等文化价值观念和“输出民主”、“人权外交”等外交现象单独列章,加以深刻地分析。
“扩张是体现在美国白人文化中的一根主线”。(第174页)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美国文化深处潜藏的“使命观”和强烈的“救赎”意识,使得美国认为它有责任为上帝散播“福音”,他们承担着使世界文明化的使命,所以“扩张”二字自古就存在于美国文化的字典里。“天赋使命观” 赋予了美国扩张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作者贯通美国的扩张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在这种观念的促使下和“孤立主义”的掩护下,美国完成了版图的扩张和国内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完善,成为了“两洋国家”,此为美国扩张的第一阶段——版图扩张。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美国的羽翼日趋丰满,它的扩张性则开始转向大洋以外,此为美国扩张的第二阶段——海外扩张(经济扩张)。这是由“美国国内经济膨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第201页)作者从两个方面指出了美国进行海外扩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一,正是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壮大了美国的经济实力,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可能性;其二,膨胀的经济使美国国内市场显得格外狭小,必须通过对外贸易寻求更为广阔的市场为经济“减肥”,解决国内的矛盾,这是必要性。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结合导致了美国海外扩张的必然性。随着经济和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美国进入了“全球称霸”的第三个扩张阶段。与旧的英法等帝国主义不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不是以武力强占为主要手段,而采取了“软势力”占领,通过将其文化价值观传播或强加给其他国家,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以实现所谓的“自由世界领袖”的梦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苏冷战也是一场文化的交锋。正如里根所说,美苏全球性冲突的最后决定力量“将不是炸弹和火药,而是意识和思想的较量。”
在全球化日趋加快的今天,美国的文化攻势也“水涨船高”。其中,作者对美国的“输出民主” 和“人权外交”作了专章的讲述。并指出所谓的“人权”和“民主”都“嫁接”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却在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里开花结果,但在“使命观”的促使之下,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称霸世界、谋求国家利益的工具。冲破“孤立主义”、走向大国合作、追求世界领导权和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参加一战的主要原因,但受“美国例外论”思想左右的威尔逊总统却给了这种行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作者引用威尔逊的话加以说明:“为我们一直所珍视的事业而战——为民主,为屈从于权势的人们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的权利,为弱小民族的权利与自由,为自由人民协力合作的普遍权利而战。这种自由人民的协力合作必将给各国带来和平与安全,并使世界本身最后获得自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2年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宣称,取得二战的胜利完全是为了“为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为保全本国和其他国家中的人权和正义”。从两位总统言语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美国文化核心“使命观”和“救赎”思想的支配下形成的,但我们不能被其华丽的词语所迷惑,应该清楚地看到民主化世界的到来只是美国全球霸权梦的第一乐章。更为可悲的是, 美国的文化输出并不具备平等的文化交流,而是要求或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其目的完全超出了文化交流的本意,美国试图使多元文化世界归宗到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统治下,以便实现一统天下的全球霸权梦,这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救世主”心态。但作者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对美国这种争做“世界领袖”的霸权梦想作了清晰的预测。他指出,在世界朝着多极化发展的今天,美国再推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政策已经很难得到他国的认同和支持,“世界领袖”的梦想对美国来说已变得可望而不可及了。原因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但无论哪一阶段的扩张都不是赤裸裸的进行地,美国总要使之与“传播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其看上去更具合理性。无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大陆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天定命论”、十九世纪末海外扩张的思想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门户开放”、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以及“输出民主”、“承担义务论”的出台,无一不具备“使命观”的蛊惑性,这都是服务于美国的扩张政策的。然而,当美国领导人将文化上的“使命观”体现在外部政策上时,往往采取的是干涉弱小国家的内政和外交,结果不但没有给那些国家带去“福音”(民主、自由、人权),相反,可能会给那些国家或地区造成更大的麻烦,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美情绪。这无疑是对美国宣称的“天赋使命”的莫大讽刺。
由此可知,正是由于美国文化中的“使命观”促发了“扩张主义”的文化意识,导致了美国从版图扩张到经济扩张再到今日的文化扩张等一系列的外交表现。相对地,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末出于美国的文化角度,通过美国这种由孤立主义到扩张主义渐占上风直至今日成为了超级大国的发展历程,得出了“中国威胁论”一说,这正是由于他没有看到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外交的实质所造成的,也从侧面反映了故国文化对一个人思想的强大制约作用。他殊不知,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美国人的“使命观”促成其海外扩张的必然性,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提倡“自我的完善”、“以和为贵”等观念,这完全不同于美国人的“救赎”思想,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之所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中国也不会走上像美国一样的扩张道路。可见,文化是一个国家外交的本质来源,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也就无所谓了解它的外交实质。
此外,作者又从“种族主义”这一文化角度阐释了美国的外交。其实,“白人种族优越主义”也根源于“上帝选民”的观念。“使命观”驱使美洲早期白人移民征服荒野,扩张版图,并自称把“文明”的种子带给了印第安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永远地把“野蛮、无知、落后”强加给了不同种族。由此产生了至今仍未消除的白人对有色人种偏见和白人“至尊至上”的种族优越心态。这种种族优越观念在美国处理对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作者就美国对拉美独立运动的态度以及美国对菲律宾、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具体分析。拉美独立战争本是西属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但杰斐逊和亚当斯都认为,由于种族的劣根性决定了拉丁美洲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取得独立,即使可以也是形式而已,由此,美国拒绝承认1801年宣布独立的现代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国家——海地。在美西战争中是否兼并菲律宾的争论中,总统威廉·麦金莱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而原因不是出于对菲律宾人追求独立事业的同情,而是不希望黄种的菲律宾人玷污了美国联邦大家庭白种人的“纯洁”。从这些外交行为中可以体现出“种族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优越感对美国外交事务的影响。
从美国文化的功利本质特征这一层面,作者又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对美国外交的重大影响。美国文化从根性上讲“向来注重实际,讲求功利,骨子里渗透着浓厚的商业气息”。(第60页)其实,这种功利主义的特征仍然与美国早期移民所信奉的新教伦理有很大的关系。“ 新教伦理把人们得到上帝的拯救从虚无飘渺的‘来生'世界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只有以务实的精神才能实现致富,成为‘上帝的选民'”。(第62页)这使得人们追求物质的欲望合理化,培养了美国人注重实际,讲求效率的性格,由此,“实用主义”便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产生并泛滥开来,而不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玄奥哲学。
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化心态给美国早期外交打上了务实的烙印。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美国民主体制的奠基人托马斯·杰斐逊、“务实典范”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曾权倾一时的亚历山大·汉弥尔顿等都曾明确指出对外事务应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一切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这种由美国开国先辈们遗留下来的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外交传统被美国后来的领袖们继承了下来。无论是威廉·塔夫托的“金元外交”、杜鲁门的“遏制政策”、“马歇尔计划”还是“ 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的出台,无一不是从美国的现实利益出发,在充分分析美国的经济利益、政治地位、军事安全、民众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和实施的。尽管有时候这些领导者的“言论”包含着“理想”的成分,但这些“理想”的口号恰恰是为了谋求利益而编织的华丽外衣。在这一点上,作者通过对杰斐逊的“理想主义”与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之争,指出“正是杰斐逊的‘理想主义',使美国在北美大陆上掀起了领土扩张高潮,最终为美国在20世纪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大国创造了客观条件;而正是汉弥尔顿的‘现实主义',使美国避开了纷争的欧洲,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发展,为美国在20世纪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第86页)在对伍德罗 · 威尔逊的 “ 理想主义 ” 外交以及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 进行分析论证同时,严正地指出“理想主义”并非有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恰恰相反,它是“天命使观”在外交中的反映,它是实现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扩张的一种手段,以期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作者指出威尔逊总统所谓的“好人政府”只不过是按照美国的政治原则和模式、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政府;而拒绝参加六国贷款也并非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美元外交”,而是威尔逊政府为了达到“门户开放”既定目标的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同样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睦邻政策”也非像他本人所说的“决心尊重自己,从而也尊重邻国的权利——珍视自己的义务,也珍视与所有邻国和全世界各国协议中所规定的神圣义务”那样高尚,而是从功利的文化角度出发制定的。固然“睦邻政策”的实施对于缓和美拉关系和促进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只是“使用政治手段、强调经济手段、限制军事干涉来达到美国在西半球的既定目的
。”(第97页)正像本书的封面所设计的那样,美国就像“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操持箭矛”的雄鹰。可见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在国家利益中是一致的。
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取材广博,史料翔实。这是建立在作者对美国文化与外交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之上的。根据作者所提供的数据,主要参考书目有50本之多,另外还有118种外文文献材料,其中有很多原始材料和有价值的新材料。此外,在吸收或介绍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些最新科研成果和针对主要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的基础之上,作者鉴别比较,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这无疑有助于学者和广大历史爱好者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再思考。例如,作者对美国早期 “孤立主义”的相对性以及《门罗宣言》的“集体孤立”目的和“孤立主义” 在美国外交中的巨大伸缩性的分析,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的阐释,并提出“欧洲均势”是美国生存和发展的“福音”,这些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使我们更直接地看到了美国外交的真面目。可谓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这充分体现了 王晓德 教授治学之严谨,方法之科学。
综观全书,可以发现无论是“使命观”所造成的“理想”追求,还是“功利主义”所造成的“现实”政策,最终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因此,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永远是主权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它永远是国家外交的核心。如果从文化对外交的影响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总之,王晓德教授所著的《美国文化与外交》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观点新颖的学术著作。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理论论证、著述风格上,无疑都具有极大的价值,特别是作者考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尤为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从文化角度研究外交,考察国际关系,为史学界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开辟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研究的新领域。这是一本不可多得,值得一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