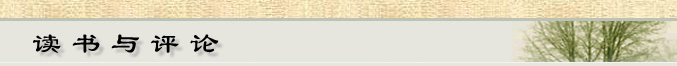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由其1961年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合而成的学术讲演集。200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本书分别从通史,政治,经济,学术,历史人物,历史地理和文化等八个题目言简意赅地论述了各自的研究意义与方法,虽然是较为随意的讲演,但是于随意之中同样透出了钱穆一生治史的严谨态度和独到识见。
诚如钱穆在本书序的开篇所言,“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书中的每个专题都体现着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取向和价值评判。综观全书,这个意义大体上可以归向钱穆于书中反复提及的一个谆谆教诲: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必妄自菲薄,应该沉潜下来,花一番工夫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的精深要义,以图对现代中国有一番切实的贡献。甚至在研读完全书之后,给人感觉更多的都是先生这种对中国历史的热爱和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并由此而生发出其对后人应当留心中国史研究的希冀和劝勉。当然,在这样笼括的意义之中,钱穆先生毕竟又论述了一些中国史的具体细微研究方法。钱氏治学,常常能得到他人如此的评价,即从很普通的材料当中研究出历史精深的要义来,我想除了其所具的扎实学养和超人洞见之外,还自有一番得体的研究方法所致。基于以上所述,本文试分别从“意义”和“方法”进行一次评述,并不避莽撞地表达个人对于钱穆先生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甚至是很不赞同的异议。
(一)
读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先,观其名,本以为是钱穆的一本单纯论述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换言之,大致应该类似技术和工具之类的书。可是,翻开书卷,刚读到序的第一句话--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我先前的想法就已然开始摇动。人都有个体自发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趋向,何况是浸沉中国历史研究功力甚深的历史学家钱穆,在那样风雨飘摇的荒乱年代,他的意欲往历史深处寻求解决现实危机方法的苦心孤诣,实在是值得后辈景仰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占全书大部分篇幅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凸现,实在是钱穆的有感而发。所以,他在第一讲“如何研究中国通史”的最后才如此说到: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两三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这字里行间,分明力透着一位史学前辈期盼有志青年来献身中国历史研究的殷殷之情。将“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作为这些讲演的“莫大收获”,由此可见,钱穆讲演的真正目的还不在于为他人提供一些简便的治史路径,更多的都是从中引发出大家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兴趣来。
钱穆当然不会只讲饱含感情的空话,他对中国传统的固守也并非是没有根据由来,通过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里头,还有许多值得人研究的价值还没有彰显出来。于是,这八次讲演,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钱穆分别从不同领域都试图阐发出中国传统当中的价值与意义,比如说中国的郡县制度,中国的考试制度,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等等,都有其巨大意义。
晚清以降,中国在世界格局的地位逐渐落后于欧美,并且屡屡遭受到列强的欺凌。于是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足取,应该抛弃传统向西方学习,才能够使中国取得进步和前进。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以一种偏激的形式向中国传统文化拉起了战旗,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等,都是猛烈抨击传统文化的斗士。在一个国家命运悬若游丝之际,诚然需要这诸多的猛士来反思和批判中国的文化病,而钱穆的出现,在另一个极点却又补足了整个局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不仅需要有专门把脉探病以去其糟粕的“医生”,比如鲁迅,而且也需要于乱世中继往以开来的平正学者,比如钱穆。朱学勤教授曾经这样说过: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这样的断定确是相当公允的。也就是说,鲁迅,胡适和钱穆,沿着各自的甚或对立的方向分开去,但都是为中国文化进行着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没有鲁迅的社会批判,不行,没有钱穆对中国历史的梳理和吸收,同样不行。
试想,当一个国家和民族接连遭到侵略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时,人们自然易对本国传统文化抱灰心甚至怀疑的态度。中国文化真的不行了吗?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应该全然向西方学习?诸如这些疑惑,定然出现于人们的脑海中。钱穆所做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生命价值的突显工作,在这些疑惑上就恰切地起到了坚固人心的作用。比如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钱穆如此劝戒:“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后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或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在《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中,他又如是勉励:“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限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书中每每多有此种言论,虽然未必都精当,但钱穆之挖掘中国文化所具之意义以图当时的苦心,确是很有必要的。
(二)
前面说到,钱穆的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不侧重于方法与技术,而在于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意义估计。但是,此书毕竟以研究的角度着眼,也就自然体现了作者的治史心得和见解。在此书当中,有相当多的方法是钱穆一生治学生涯中积淀的精华。通过这些方法,历史精髓的要义总会明白的显现出来,当然,在这本书中,主要还是钱穆认定的中国文化一直存有但为时人轻视的价值。
例如,钱穆在论及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一讲中,首先即从中国人对待物质经济的传统心理出发,他指出,中国人不同于西方“无限向上”的人生态度,而是满足于“经济之水准”。掌握了这一文化特征,研究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各朝各代的经济政策,乃至农工商业所占地位之轻重及其原因,就有了一把开启的钥匙了。比如中国的休养生息政策,中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经济心理,无一不是从前面说的文化心态生发出来。钱穆之所以有此识见,前提在于他的另一方法,即在“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的认识论基础上提出的: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做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可以说,这也就是钱穆研究中国历史整体的方法。他认为,无论社会政治还是经济,其实都可以归向于文化,每个领域的研究,断然不可以各相分离。
平常,人总以为历史乃是以往,研究历史即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钱穆则不以为然。“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联系合一来看”。他认为我们在研究过往历史的同时,还应该好好把握住现在,因为正是现在构成将来的历史,我们今人自然应该为后人留下研究我们当代社会的便利。在研究前代历史时我们感叹前人留下资料的稀缺,而自己又不在意当前资料的存留,这是怎样的遗憾,所以,钱穆倡导的注重当前社会研究的方法是深具意义的。
当然,钱穆有些研究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甚至质疑的。比如,在《如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中,为了说明中国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的特征,钱穆拿中国和整个欧洲相比。相比之下,欧洲就显得纷乱和隔离。这样的结论自然是不错的。可是,首先要注意的是,比较的对象是否得体?中国能共通和融合,实乃民族凝聚力所致,欧洲虽在整体面积上可与中国相比,但是其中居住的各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呈现出来的自然各不相同。所以,更不能以此而论证中国文化的伟大。我想,如果用一国单比另一国,甚或会更合理一些。
(三)
如前文所述,钱穆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梳理和对其意义的彰显,以图对中国社会发展尽力。这种平正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人们尊崇。但是,他提出来的一些看法,人们也是应该值得留意的。钱穆自己在八讲最后总结到说“有时不免带有情感”,我认为,这既是一个儒雅学者的谦虚之言,同时也是确有其事的。
钱穆担负着传讲中国文化的重任,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中国历史总有一番赞誉。在这本书当中,很难看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比如赞扬中国郡县政体之伟大;在当前欧美考试制度优越于中国的事实上,回溯到考试制度最早产生于中国的历史;反复阐述中国人本主义的传统;如此等等。如前文论述,这样的工作可以起到稳固人心增强国人自信心的作用,不应该太过苛责。可是,有些处钱穆确是“带有感情”而有所夸张的。
比如,钱穆提到的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在许多儒家学者的著作中,确实多有提及关爱百姓的言论,最明显的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钱穆说的经济方面满足于“经济之水准”的心态,可以轻松走上人本主义的道路,也都属实。但是,人本主义其实更多也就是停留在学者的著作中和统治者的口头上。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无论盛世还是乱世,受苦的总是黎民百姓,何有真正的人本主义关怀?是的,儒家学说多有提倡爱惜人民的理想和抱负,可惜的是,却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真正实现过。蔡元培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序文中这样描述:“自此(指诸子时代)以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湮塞,士论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罢黜某某,文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人,曰以拥护君权为能事,有预约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火其书而刑其人”。由此可见,若说中国有真实的人本主义,那么也就仅仅只以一人为本,那就是君主。至于其他的人呢?鲁迅洞若观火,言简意赅地道出二字:吃人。
另外,钱穆在论述中国历史的时候,时常不忘和欧美国家比较。明处里说中国文化之优越性,而暗处又有西方文化之低劣性之指点。当然,只要举证属实而又结论得体,自然是无可指责。可是,钱穆在有些处得出的结论或多或少有所偏颇。如在《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中,钱穆认为中国人生美化艺术化,西方则机械化,中国属仁义方面,西方核子武器之发明是大不仁。其实如果比较起来,西方的艺术并不亚于中国,只是风格品味不同而已。至于核子武器,我也认为是弊大于害,可是离钱穆此时不远的中国抗战时期,如果没有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中国处于被日本侵略的水深火热中的时间甚或更长?可见断然认定中国优于西方,未必就是妥恰的。钱穆此言论的根基在于人性善恶论,他认为人性善就是可取,可是,面对恶的时候又怎么办?很多时候善对恶却无能为力。那么,我们或许更应该对可以降伏恶的一方更多一些尊重和宽容。
又如在论中国历史人物上,钱穆说,“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这样说固然没错,但是一个“惟有”,不免有所偏狭。细想一下,哪国哪民族在危难时机何尝又没有自己的大魄力大胸怀的英雄?总体而言,如钱穆自己所说,确是颇带情绪的。他的良好情操,他的爱国情怀,经由他个人的精神气质和研究方向熏染,或多或少使他转向了保守和自大,太看重了中国而轻视了外邦。这样自发的动机固然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但是对于结果中不太合情合理的成分,我们也应该指出和修正,哪怕,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身也不合情不合理。
参考资料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2]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3]余杰:《文明的创痛》,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