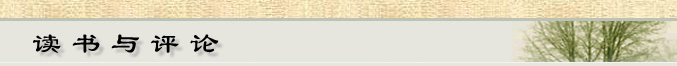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中华帝国的法律》读后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硕士 李佳
《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为美国学者D·布迪与C·莫里斯合著,前者为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著有《中国思想西传考》、《古代中国的庆典》等,并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后者则任教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著有《律师如何思考》等。《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是迄今为止西方汉学家在古代中国法律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作者从清代案例汇编《刑案汇览》中精选出190例,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与评议占全书的过半篇幅,此种美国式案例分析研究法是本书特色之一。展读此书,不但可以较全面的了解清代法制,而且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当有亲切的认识。下面,笔者即就其具体内容展开介绍,兼以评议。
一、基本框架与大体内容
《中华帝国的法律》38万字,381页,书分三篇。第一篇:中国法律初论。在这一篇中,作者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概括性考察,从纵向渊源上说明清帝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无论从立法思想还是实际规程上都有其“一贯的血统性,其间对礼法相入的问题亦有一定探讨。重点在于向读者介绍本书后文所采用的190个案例的来源——《刑案汇览》。《刑案汇览》实际上包括各自独立的三种汇编,即:
《刑案汇览》、《续增刑案汇览》、《新增刑案汇览》。此三种汇编皆为清人所作,共收录自乾隆元年(1736)至光绪十一年(1885)近150年间7600多件案例,案件发生的年代主要集中于19世纪的前30年,尤其是1811—1830这20年间。第二篇:清帝国案例评析。在这一篇中,作者以名例律类、吏律类、户律类、礼律类、兵律类、刑律类、工律类为别,以190个案例按类相从,且每个案例后附有长短不一的评论,这构成本书的主体内容,亦是本书最有特色的部分。第三篇: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在这一篇中,作者对清朝法律作了一定篇幅的评论,认为清朝法律律义清晰,而且超出文字的拘宥,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背离法律条文的表现,但是“罚当其罪”的主旨却在事实上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认同。
二、所见案例之分析与思考
《中华帝国的法律》不仅从司法角度探讨了古代法律条文的制订问题,还大量(190例)分析了具体案例。“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事实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该书所引案例则试图反映法律条文在非特殊条件下对平民案件所发挥的实际效能,这对于我们探寻19世纪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有莫大助益。“简言之,我们希望通过释读这些案例,有助于弄清为什么中国的君主制不得不于1911年让位于共和制……这些案例的绝大多数都发生于文化和政治上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风暴马上就要来临……1793年至1839年这半个世纪中,虽然中国已经开始衰落,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时有发生,但从外部来看,仍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这段时期也构成了中华帝国‘常世’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它的法律制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未受任何西方影响侵蚀的固有的法律传统。”(p.140~141)下面,笔者就于该书摘引数例案件,略加说明。
案例57.1(道光六年)
王五因时向耿育才借贷钱米,均不记数。迨后耿育才因其屡次缠绕,不允借给。嗣王五因贫难度。伊子王雨儿瞽目坐食,起意致死、免累。将王雨儿摔倒在地,揢其喉咙、殒命。
对于此案的分析,作者除了说明由于维护尊长的权威,法律对于杀死儿子的父亲常常网开一面,表现出特有的宽大处理的原则。即父亲无正当理由而杀死儿子,刑罚仅为杖六十,徒一年。同时,作者还直截了当的指出,“贫困”实为此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案例70.1(乾隆三年)
李昌因恨李茂(李昌胞弟)不给豆石花费,乘醉携刀寻闹,由粪堆爬墙入内。因失手倒栽墙下石上,磕伤聪门偏右。李茂奔告胞叔李淑斌,赶到目击劝解。迨后李淑斌又因其头带血痕,用布包裹。则实系跌伤有据……至李昌已将弟家铁锅打破。李淑斌趋至喝阻,不听。复持刀逞凶,向扎。李淑斌喝令李茂殴打、夺刀。李茂用拳殴其左右肋,不能夺刀。复棍殴臁肋,倒地,始将刀夺下。李淑斌代为包裹,送回。李昌将包布揭开,伤处进风,越八日抽风殒命。则李昌聪门实系自行跌伤,死由抽风,毫无疑义。但李茂殴伤李昌左右肋,虽系伊叔教令、伤非致命,实属有干伦纪。应如所题。李茂合依“弟殴胞兄、伤者,杖一百、徒三年”律,量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对于此案的分析,作者认为在判定李昌纯属自伤致死的基础上,仍然对李茂处刑,且量加一等,而指令李茂殴打李昌的李淑斌却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案件的判处结论带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当一名卑幼听从尊长的命令而对另一名尊长实施暴力犯罪时,这名卑幼该当何罪?卑幼必须服从尊长的命令,而卑幼对尊长实施暴力犯罪又是法律严惩的对象,这两项原则互起冲突,使得案情复杂化。
以上案例57.1和70.1都一定程度地说明了家庭关系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地位,一旦案件涉及“五服”,无论是法官还是案件涉及的原告、被告都必须首先服从伦常的制约,事实上,即使是如案例中对杀子之父王五的轻判和李茂因令殴兄的重判,在19世纪的清朝社会都是被毋庸置疑的认同,或强制认同的。即如作者所言“儒家社会所特有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家庭成员等级差别中有最明显的表现——这种等级差别是用五服制来精心加以度量的。”(p.137)对于这一点,瞿同祖先生亦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有过论断:“法律在维持家族伦常上既和伦理打成一片,以伦理为立法的根据,所以关于亲属间相侵犯的规定是完全以服制上亲疏尊卑之序为依据的。”
案例18.1(乾隆五十七年)
陕西省题武小孟因刘仰儿等摘伊地内豆角,踢伤刘仰儿身死一案,将武小孟依擅杀拟绞(监候),均经照复在案。
对于这一案例的分析,作者认为受害者刘仰儿在武小孟案中未作任何反抗行为,但因他犯有盗窃罪,被确定为“罪人”,所以判定“罪人不拘捕,被擅杀。”但是更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作者将此案与案例57.1归为一类加以分析,认为两案都可能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财产匮乏的情形。在总体背景是前工业化的农村社会中,贫穷以及争取生存的不懈斗争是生活的突出任务。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来说,只能无条件的实践着这种缺乏选择机会的生活方式,而别无他途。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笔者认为贫困是犯罪的唯一致因,只是强调这一案例恰恰反映出当时中国农民对财富的初级表现形式——粮食的渴求与重视。
案例92.3(嘉庆十四年)
廖五虽屡被熊大才讹赊酒钱及抢夺被褂,尚无逞凶情事。至熊大才强拉邹英家牛只卖钱,并强奸彭王氏未成,均与廖五毫无干涉。该抚(陕西巡抚)将该犯依“杀死凶恶棍徒”定拟,与例不符。惟熊大才抢夺廖五褂被,本属抢夺罪人。廖五系事主,纠同戴子耀等殴打泄忿,已将其按倒,尽可拘送执官,乃辄砍伤致毙,实属擅杀。廖五改依“罪人已就拘执而擅杀、以斗杀论”律,拟绞监候。
作者认为案例92.3给人的印象是作出终审判决的刑部无所不知。刑部总是知道所有的有关事实——而且自我感觉良好。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司法机关的实际调查以及对那些拒不招供的犯人或证人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行使拷讯权。但似乎还有另一个因素可能更为基本:“那就是在一个由绝大多数文盲构成的社会中,由少数精英组成的官僚集团应当拥有无上的知识的这一心理需要。”(p.131)在一个不允许任何私人法律职业者对自己构成挑战的司法制度中,司法机关很显然是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和错误的。
案例64.1(乾隆五十年)
刘万禄先与刘老屋同赌,被其赢得钱文。嗣刘老屋复与赌博,不允;乘醉詈骂。刘万禄不甘,因己身残废,恐力不能胜,主使在店住宿之李虎山、陈四海、并雇工王际桂殴打。刘万禄走出查问,因刘老屋并未输服,将其鞋、袜拉脱,复令李虎山等殴其腿腕等处。刘老屋被殴求饶,声言、磕头。刘万禄始令住殴。刘老屋越十日因伤身死……刘万禄虽属残废,而李虎山、陈四海系伊店内住宿之人;王际桂又系雇工,均属依伊居住,是有不得不从之势。该侍郎将刘万禄依“主使之人为首”律拟绞,洵属妥协,似可照覆。该司以刘万禄并未殴打,议将在逃、下手之李虎山拟抵,而将主使殴打之刘万禄照“原谋”拟流。揆之情法,未为平允,应请毋庸议驳。
作者在分析案例64.1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某人明知某项行为是错误的,或者是非法的,但由于受到他人的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而实际从事该项行为时,他应对该行为负有何种法律责任?“在一个高度权威化的社会群体中,下属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意志。在经济不发达以及前工业化社会中,由于个人在营生之道方面选择的余地过于狭窄,因此,也普遍存在集权化社会群体中下层人士无条件服从上层人士的现象。”(p.239)案例64.1的情况即是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如果李虎山与王际桂不服从店主刘万禄的命令,前者可能即被驱逐,后者则处于被解雇的危险境地,那么他们也一时很难找到新的雇主,因而失去营生之道。这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结合,迫使雇工等惟有“不得不从”一途可走。
法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以刑事制裁为其中心任务,在这一点上,历朝法律皆因循承袭。而其制裁的内容指向,虽各朝由于时代背景的演进,主要指时间上的推移,如由明而清;或者因为立法主体的特殊性,如元、清以少数民族问鼎中原,而存文字上的不同和技术性的差别,其律文的主体部分实在多于“沿”,而少于“革”。本文从《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摘引数条案例,即试图传达作者于字里行间所蕴含的这种对清朝法律缺乏变通性的质疑。无论是对宗族主义的无条件服从,抑或仍然极大左右下层民众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是政府部门凌驾于事实之上,无可争驳的主观判定权,19世纪的中国法律都予以毋庸置疑的肯定。此外,如果我们赋予法律一种抽象的框架性,那无论是立法者,执法者,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应守法者,事实上都无力置身于这一框架之外。即使是社会的最高主宰者——皇帝,其“违法”的行为亦应处于尚可逾越的范围内,否则逾越行为将可能会不同程度的损害其自身的利益,因为对于皇权来说,法律所维护的秩序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推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被束缚于法网之中,而成就这张法网经纬的各项法律条文又缺乏必要的新陈代谢,其产生实际效能的消极方面无异于作茧自缚,整个社会的进步亦无疑会处于令人担忧的境地。在以“变革”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由流于传承的法典透视整个社会,利于形成质变的积极发展因素的量的积累,始终不能达到破茧而出的程度。最终,中国人失去的不仅仅是大清律法的尊严,而更是此后百年注定的国运坎坷。
三、问题
《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对清帝国的法律与社会做出了卓越的探讨,既在史料分析上质量兼优,又为我们研究清朝历史发展轨迹提供了以往较少注意的法律视角。但是在我们从该书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存在的个别问题。首先,该书选录的190则案例皆来源于《刑案汇览》,实际上《刑案汇览》包括各自独立的三种汇编,即:
《刑案汇览》、《续增刑案汇览》、《新增刑案汇览》,共7600多个案件。虽然从7600余例中摘选190例,相对前人足称突破,但就其论据与论点的是否对称,仍需谨慎对待。在案例7.1中,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儿到邻居地里捡了一把黄豆;在案例18.1中,一个13岁的男孩儿路过邻居的果园时捡起了三只梨;在案例98.1中,一个老妪带着小孙子在路边捡起邻居收割时掉落的麦穗。以上这三起琐事都导致了暴力和杀人,进而作者得出结论“只有在中国农村,这三个涉及在田里捡麦穗的案子才会发生。”(p.124)显然,基于三个案例就判定中国社会是发生此类案件的唯一环境,是不够慎重的。其次,该书所选190个案例以名例律类、吏律类、户律类、礼律类、兵律类、刑律类、工律类为别,每一类别内又分为若干条目,各条目下有一至四个案例不等,但各案例之间的编次却稍显凌乱。例如,在刑律类43“恐吓取财”条目下有三个案例,作者将其按年代依次排序,即:43.1为嘉庆六年案件,43.2为嘉庆八年案件,43.3为道光八年案件。而同样是在刑律类别内,62“斗殴”条目下的三个案例却没有按照案发年代排序,即:62.1为嘉庆二十二年案件,62.2为嘉庆二十四年案件,62.3嘉庆二十一年案件。
《中华帝国的法律》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国法律的重要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选录的具体案例非常客观地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的实际图画。作者认为“所引案例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向世人表明古代中国存在着犯罪,甚至包括最可怕的犯罪——这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而在于它们展示了某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包括那些一直延续到最近的制度。”(p.160)展读该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有关清朝法律的内容,还利于启发并加深读者对于那个时代的思考。虽然书中存在个别值得商榷之处,但从总体来看,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