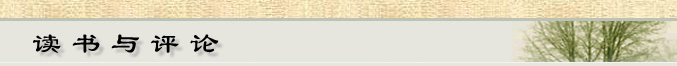雷海宗(1902-1962)先生是20世纪我国极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终身致力于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哲学功底厚实,史学理论自成体系,见解精深独到而著称;其门下弟子桃芳李菲,成绩卓然,他们或为学界领军人物或为一代名师,继续传承和发展着雷海宗先生的思想体系。如今,伯伦先生虽已辞世四十余载,但其治史方法与门径、学理系统与观点等仍为史学界热烈研究、探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下文简称为《中》)一书是雷海宗先生的代表著作,涵纳了其史学思想精要之大部,是学习和研究雷海宗先生整体历史体系必备之参考文献。它最早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2月出版,因时代渐久,40年版《中》书已难见到,所幸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复出此书,两年后又再次印刷,方使后辈学人得以瞻阅,不落遗憾。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集合了雷海宗先生多篇论文,全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宏富,叙述稍轻,说理为重,分析深透,充分展现了作者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与浓重深沉的爱国情愫。书中,雷海宗先生以中国文化发展规律为考察核心,以尚武精神兴衰为探讨主线,创造性地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中国文化两周说”理论,将中国四千年历史划分为两个生命周期。卢沟桥事变后,雷海宗先生分析了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文化新生之意义,热情地呼唤了“在望的第三周文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文化周期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初版距今已然六十余载,但为先生所预见的第三周文化却正在拉开帏幕,体系独具的中国文化周期论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流派中不容忽视的一支。许冠三先生便在《新史学九十年》中专辟一章讲述雷海宗先生的文化形态史观,《中》书亦是其主要参考资料之一。《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体大精深,读之受益。在此,笔者将简要介绍该书的基本结构、大体内容,评析该书的核心理论——“中国文化周期论”,以期与众师友共同探讨、深入理解之。
一、《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基本结构与大体内容:
《中》书分为上编、下编和附录三大部分,其大体内容如下:
上编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等五篇文章,它们是雷海宗先生于“抗战前三年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序》p.1.)其中,前三篇主要从军队、家族和皇帝制度上关注了秦以前的中国,第四篇则专讲秦以后的中国,第五篇总论整个中国历史,它们虽然探讨具体相异的问题,但却无一不是对“中国旧文化批评估价的文字”
(《上编•总论》,p.1.),因为只有通过批评与估价,国人才能正确认识旧有文化的优长与劣短;而只有清醒地认识旧文化的优劣,特别是不足之处时,方可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笔者认为这正是雷海宗先生写作《中》书的主旨所在。于此主旨下,《中》书无处不谈及文化、关注文化,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切入点和突破口。在《中国的兵》一篇中,雷海宗先生谈到,历代史学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重于制度方面,而忽略了兵的精神。事实上,制度变迁不过为一个“格架,本身并无足轻重”(p.2.),而探讨兵的精神才是明了一个民族胜衰的方法。在《无兵的文化》一文中,雷海宗先生划秦为界,认为“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p.102.),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尚武精神的缺失,在于“无兵的文化”。春秋时代,男子以当兵为至高荣誉,成为一名勇武的战士甚至是贵族方可享有的特权。而秦以后,一种完全消极的“无兵的文化”主导了历史的演进过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pp.101-102.),终使中国政治制度凝结,发展停滞。上编的第五部分,雷海宗先生首先阐明历史研究中分期断代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历史就是变化,研究历史就为的是明了变化的情形。若不分期,就无从说明变化的真相。”(p.131.)然而,中国学人惯于套用西洋史学的方法——将中国历史笼统划为上古、中古、近代,此作法既不科学亦不可用,“比不分期也强不了许多”(p.132.)。因此,雷海宗先生在比对中国历史与其他民族历史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果敢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两周说。
1937年7月后,抗战烽火燃遍中华大地,隆隆炮声打破了清华园往日的宁静,雷海宗先生在亲历了“素日领受微薄薪饷并被轻视的大兵,在前方喋血抵抗”(p.169.)的惨烈悲壮后,对中国文化的意义进行了新的探讨。在保持旧日见解大体不变的前提下,他将先前集中于传统文化弱点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上,以声扬抗战意义和士兵舍死忘生精神为主题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展望中国文化新周期的《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被收录在《中》书的下编中,它们与上编五文相互论证,彼此补充,使中国文化周期理论更加完备。伯伦先生认为,抗日战争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它是中国结束旧文化局面、创造新文化周期的最佳契机。赢得抗战的胜利,并圆满解决三个问题——属于民族文化层面的“兵的精神”问题,属于社会层面的“家族”问题,属于政治层面的“元首”问题,“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p.183.)
《中》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雷海宗先生《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殷周年代考》、《君子与伪君子》、《雅乐与新声》与《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五篇论文,它们不仅在各自专业领域很有影响、颇具学术价值,且为研究伯伦先生史学思想的珍贵资料。
二、中国文化两周说
雷海宗先生早年留学海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修习历史与哲学,并获博士学位,不仅专业素养极高,接受新思想、新理论的能力也很强,本着兼容并包的态度,他“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学说都加以“注意和钻研”,并自觉地以哲学观点为指导理解和分析历史。归国后,雷海宗先生曾于清华开设“西洋史学名著选读”课程,讲授包括斯宾格勒《西方之没落》在内的西方典籍,其历史观及史学体系亦深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的影响。在文化形态史观的指引下,雷海宗先生陆续发表文章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并最终创建了中国文化两周理论系统。
欲立新说须先突破旧有观念。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错误倾向(笔者认为这两种错误倾向至今尚未完全避免)。其一是轻视断代分期的价值,认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p.131.)的问题;其二是“不负责任”(p.132.)地将西方的划分方法原封不动搬来,强行套用在中国历史上。针对此上两种谬误,雷海宗先生首先完成了为历史分期问题“正名”的工作:重申断代分析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批判了简单粗暴的中国史三段论。雷海宗认为,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方法本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它羼杂着当时文人对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眷恋之情,且因这种崇拜古代的心理始终未被消灭,历史分期的三段论方渐被公认。19世纪中叶后,西学在中国影响日广,不少西方学说皆被奉为“金科玉律”,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再完备的就是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这种分期法倡于何人,已无可考,正如西洋史的三段分法由何人始创的不可考一样。但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p.135.)
那么用怎样的分期或断代方法来解释中国历史才比较圆满呢?雷海宗先生以中国文化为分析、考察对象,详尽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文化两周论。其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的中国为古典的中国,由最初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是政治、文化的重心,长江流域仅处于附属地位。除所谓的史前时代以外,第一周的中国历史可分为五个时代,分别是封建时代(公元前1200-前771年);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3年);战国时代(公元前473-前221年);帝国时代(公元前221-公元88年);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383年)。
封建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全被纳入宗教之下,各种神祗遍布天上人间,自然现象均被神话。春秋、战国以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为界,此前的春秋时代,大小诸国名义上仍承认周王的共主地位,其战争是意在维持均势的战争;战国时代则全然不同,诸侯交战均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毫不留情地灭绝对方以强盛自己,这是战国时代独有的“战国精神”。春秋大部分时间仍在宗教统治下,至末期政局变动,独立的思潮渐渐兴起;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动荡的时局反促使思想家们积极探求强国、统一之途,他们各自提出一套理论并为实现自己的学说奔走呼号、争论不休。春秋时期,当兵仍是贵族阶级的权利与荣誉;而至战国时代,征兵制出现已成定局,当兵成为普通百姓的义务。“所有战争都是以尽量屠杀为手段,以夺取土地为目的的拼命决斗”(p.149.)。帝国时代,国家政治统一,经济强盛,文化上的争鸣失去存在的必要与空间。汉和帝一代(公元89-105年)是帝国向末世过渡的重要时期,此后帝国的衰退日益明显,内政破坏、外族势力渐强、中原民族的尚武精神消失。精神方面也呈现衰颓之态,“儒教枯燥无味,经过几百年的训诂附会之后,渐渐被人厌弃”(p.151.),消极的老庄学说受到青睐,佛教也开始进入中国。
第二周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至抗日战争前。这一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屡次入侵中原,印度佛教不断渗入并最终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化学的作用”(p.152.),中国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巨大变化,已不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一个胡汉混合、樊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一个向南方大发展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但外来的成分却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第二周中国历史同样可分为五个时代,各以时代为名(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属名称,而第二周各代只以朝代为名。这是因为,雷海宗先生断言秦以后的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即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383-960年);宋代(公元960-1279年);元明(公元1279-1528年);晚明盛清(公元1528-1839年);清末中华民国(公元1839年以下)。
南北朝、隋、唐、五代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南北朝时,少数族与汉族同化,佛教与中国旧有文化融合;隋、唐作为一个胡、汉合作的二元大帝国,天子对内称“天子”,对外则称“天可汗”;安史之乱后政治开始衰微,文化发展滞缓。宋代的三百年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王安石变法整顿各种政治积弊,宋代理学整顿思想观念,佛教被最终接受。元、明两代是失败与结束的时代,有元一代百年间,中原民族首次受制于外族,传统文化遭受到空前的压迫与排挤;明代科举制度变得僵化,政治日渐腐败,宦官当权干政,思想界亦缺乏生气,“整个民族与整个文化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在这种普遍的黑暗之中,只有一线光明,就是汉族闽粤系的向外发展,证明四千年来惟一雄立东亚的民族尚未真正的走到绝境,内在的潜力与生气仍能打开新的出路。”(p.157.)晚明、盛清是政治文化完全凝结的时代,政治上没有发展进步,文化上没有更新创造,空耗了漫漫三百年光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衰势已然非常明显,处于濒临全面崩溃之境地。
三、中国文化即将进入第三周
1937年后,抗战烽火将整个中国烧得通红,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胜负未卜的战争结果和吉凶难料的国家命运,雷海宗先生非但没有悲观、沮丧,反而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与信仰。他以笔为戈,投身战斗,分析了此次抗战对于中国文化新生的伟大意义,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伟大,抗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p.171.)“成败利钝,长久未来的远大前途,都系于此次大战的结果。”(p.177.)他大声呼唤国人尽快从和平的迷梦中醒来,拿出我们修养生息了两千年的元气“与亘古未有的外患相抗”(p.176.),坚定必胜之信念,以“战国精神”应对“战国时代”。
雷海宗先生坚信,中国文化虽然古老却仍富有朝气,只要我们赢得此次抗战的胜利,中国文化就必将新生。就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雷海宗认为,抗战中的中国正处于第二周文化与第三周文化的交界点,“从任何方面看,旧的文化已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新的文化有必须建设的趋势。”(p.178.)而理想中的新文化应是类似“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p.181.),既不提倡暴躁、残忍的纯武德,更反对虚伪、卑鄙的纯文德。国难当头之际,首须强调武德的重要,面对凶悍残暴的侵略者,国人应该挺身自卫,担当为国家民族拼命的斗士;和平建国阶段,处于社会领导地位的人、文人学士也该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社会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风气;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p.181.)
中国文化即将进入第三周说是中国文化两周论的发展,它进一步充实了雷海宗先生中国文化周期理论的内容。历史证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非但没有亡国灭种,反而蓬勃新生。新生的中国文化宛若初生婴儿,向世界展示着它惊人的生命力与生长力,这一点已被雷海宗先生言中。那么中国文化何以有如此长的寿命呢?伯伦先生阐释到,每一文化发展都由分裂的小国开始,小国合并为大国;大国兼并,相互厮杀,最后由一国吞并列国,一统天下,成为统治整个文化区的帝国;帝国末年,政治腐败,文化衰颓,于是走向分裂、灭亡。其他国家遵循这一规律,至此都无从维持,一周而亡。唯有中国,“于秦汉统一打帝国之后,虽也经过三国六朝的短期消弱,但后来却又复兴。复兴之后,政治制度虽不再有多少更革,文化潮流却代有进展。这是其他民族的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p.173.)因此,作为一个生活在第二、三周交替时代的中国人,虽不免痛苦却又是无上光荣的:“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战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p.184.)
四、结语
如果说中国文化两周论是对中国四千年历史进行的系统梳理与切割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即将进入第三周说则是对中国前途的预见与展望,二者合而为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周期论”。虽然,在其理论中我们还遍寻不到任何历史发展、进步的痕迹,但唯独中国文化可循环往复、多次新生的理论在当时仍是领先的,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上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之风复在中国学界卷起波澜,为数众多的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学习、介绍、宣讲舶来理论的潮流中去,意欲从中觅出强国兴邦的法宝。1918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西方之没落》问世,率先阐述了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方法。其后,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的《历史之研究》陆续出版,文化形态史观的架构更加完备,内容更加充实。在张荫麟、张君劢等人的积极引荐下,文化形态学传入中国,然而影响甚微。直至雷海宗、林同济、陈铨主导的“战国策派”形成,文化形态史观方才受到广泛关注,学人始知于旧有方法之外还可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分析历史、解读历史。雷海宗先生既以中国文化为研究重心,结合政治制度、宗法传统等因素,捋顺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探讨其演进规律,视角独特而新颖,就此提出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即便今日,文化形态史观仍不失为有效、可用的理论工具,借此分析中国史或西洋史,或有不意收获。
近代中国贫弱被欺,思想文化亦显落后,就在知识分子开始置疑、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学术之际,西学汩汩而入,终被奉为经典。崇洋渐渐成为一种潜意识悄然渗入中国学人的骨血,西学理论、规则、范式、概念等等被四下套用、滥用,中国历史三分法也是此类产儿。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雷海宗先生追根溯源,毫不隐讳地指出笼统的历史三分法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它套用、照搬西方理论,对研究中国历史有害无益,一改当时学人盲目附会西学的惯势。举一国之全史巴结西学某一社会演进理论,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附会西方经典是中国史学长期处于欧洲中心论阴霾下罹患软骨病之表现,雷海宗先生虽以文化形态学作为理论导向,但“中国文化周期论”始终根植中国本土,并极力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桎梏,认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皆有不同且优于其它文化,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中国历史独具多周理论是雷海宗先生在充分研究中国历史,充分关注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亦远优于三分法的牵强附会。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始终给予现实社会以特别关注,其问世时值抗日战争进入最紧要关头,因此,伯伦先生的“中国文化周期论”不仅在知识界颇具影响,即便是普通民众阅读此书亦无不为之砥砺士气、鼓舞精神。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文化多周期、长寿命理论的提出非常鼓舞人心,发人奋进,坚定了国人必胜之信念。即便今日,抗战的硝烟已散去整六十年,再读《中》书亦使人觉得精神百倍,民族自豪之感溢满胸口,这是一代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以满腔爱国热忱及无限史学智慧捧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笔者深知单凭一部《中》书来分析雷海宗先生全部史学思想要义是远远不够的,即便专以讨论中国文化周期论亦显不足,谨述于此,期待广大师友教导、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