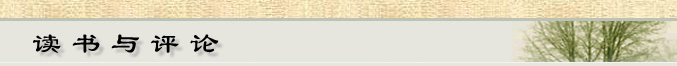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
读《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3级博士研究生 闫瑞
[提要]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兴盛时期,沈定平先生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试与会通》一书,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以及明代社会变革造成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创造了良好文化氛围这两条历史线索,展示了交流的双方——西方传教士与明末士大夫——在交流中做出的积极努力,以及他们共同营造的明代中西文化交流调适与会通的面貌。沈先生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厚的了解,且对其强大的包容性颇有信心,该书结论部分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但先生的研究立足于详实而丰富的史料,且试图在中西学者对这段历史不同的解读中找到平衡之处,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关键词]明代;中西文化交流;调适与会通;适应性传教策略
沈定平先生长期以来从事明史、中外关系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后来又集中于明清之际(16-18世纪)中西关系史,包括两大序列,即明清之际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和影响,以及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下文简称《明代:调适与会通》)一书,就是后一序列的反映。该书最早由商务印书馆于2001年出版,增订本于2007年仍由此出版社发行。正如沈先生自述,“本书的重点在于揭示中西文化之间同一与互补的关系,内容涉及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和较为平等的文化交流机制的建立”,[1]书名“调适与会通”是理解本书的关键,也是沈先生所认为的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境况的主流。沈先生清楚地知道,随着交流逐渐深入,彼此间的差异性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也在日益显著,但因与此书的主旨“调适与会通”有所不同,故将其移置于以后的研究中。2012年沈先生就已出版了《明季:趋同与辨异》一书,论述利玛窦病逝后明末及南明七十多年的中西交往史。据沈先生所述,关于清代的中西交往史仍在撰写中,鉴于先生深厚的史料、学术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此书当很值得期待,现只有静待佳音了。现将我从《明代:调适与会通》一书中的收获记录于下。
一 以两条历史线索为主的全书架构
《明代:调适与会通》全书共有十章,我认为可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全书研究的时空背景,包括第一章“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与第二章“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书中大致梳理了汉、唐、元时期基督教以不同形式进入中国的历程,到了本书重点探讨的明清之际,近代西方殖民势力的发展,欧洲近代科学革命与人文主义思潮,使得中西文化进入了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和交往的新时期。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到第七章,进入该书的中心内容“调适与会通”,主要讲传教士的努力,“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出炉过程,沙勿略与范礼安的酝酿与策划、罗明坚的早期实践活动、集大成者利玛窦的传教活动,以及适应性传教路线最终形成并有了理论总结,最后比较了适应性传教路线同传统的军事征服传教路线的分歧及其影响。
第三部分包括第八章“明末的统治危机、社会思潮和西学传播的文化氛围”与第九章“明末士大夫的西学热潮及其代表人物”,这是“调适与会通”的另一角度,关注点是为交流提供可能性的明代社会,书中探讨了在明末士大夫中何以形成了“西学热潮”。
第二、三部分,正是按照沈先生所说的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两条历史线索而写,“一条是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国情有所认识的前提下,逐渐抛弃在当时基督教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将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紧密结合的传教路线”,“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形成的过程;“另一条历史线索,则是明中叶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呼唤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多元化趋势”。[2]这两条线索,也正体现了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中西双方都主动性地寻求共同性与互补性。
第四部分,第十章“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调适”,这是一个关于本书主旨的个案研究,交流的双方——明末士大夫的代表徐光启与传教士的代表利玛窦——分别做出调适中西文化的积极性尝试,这一部分也联通了第二、三部分。
仔细阅读完此书,深感沈先生学术功底的深厚,尤其是在本书的主体时间段——明清之际,丰富且翔实的史料考证让人信服,现将使我感触颇深的几处阐述如下。
二 书中精彩之处
1
“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
个人认为,此书最精彩的地方是在第二部分,对“适应性传教路线”的研究。“适应性传教路线”是沈先生对利玛窦等中国传教士传教路线的明确定义,且将其作为《明代:调适与会通》一书研究的主体部分,进行深入研究。沈先生提出,“这种策略并非一蹴而就,它既取决于欧洲和中国所特有的思想文化源流与客观的环境,也有一个酝酿、探索、实践到形成的过程。同时,这不只是利玛窦个人的贡献,而是对在此之前的沙勿略、范礼安和罗明坚开创性工作的继承与发展。”[3]
那么,何为“适应性传教路线”,且为何强调“适应性传教路线”呢?
“适应性传教路线”是以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为代表的,“以和平方式和学术渗透为特征”的传教路线。如此强调它,这是要与在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占主流地位的“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的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紧密联合的“军事征服传教路线”相区别。“所谓适应性策略就在于,这些传教士‘准备放弃其偏爱祖传的西方风俗习惯的人类偏见,准备放弃基督教中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基督教附属的西方外部标记,但是不准备放弃基督教的本质。’”[4]
沈先生用了四章的内容来展现“适应性传教”,从一生未踏足中国内陆的方济各·沙勿略,到广受明末士大夫推崇的利玛窦,“适应性传教”从一个策略最终成为明确实行且被后人坚持的路线。
对于沙勿略的贡献,沈先生认为有三点值得称道:一是他“选定中国作为东方传教的中心,并通过不懈的呼吁、书信介绍乃至以身殉职,初步引起了罗马教廷以及欧洲社会对于这个东方大国的关注,从而为未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二是他在长期的传教经验中认识到,“古老东方的文化和宗教中亦蕴涵着人类的真理。即使为了最终达到使人归化的目的,也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居高临下、排斥一切而迫人就范的传教方法,提出了‘学术传教’的设想”;三是他主张“采用当地语言和思想文化观念进行传教”,尝试将“基督教义同当地流行宗教”进行某种结合。[5]
在沙勿略殁后二十余年间,耶稣会士急切地想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为此,他们“一方面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提高澳门在传教中的地位,兴建学校、教堂等公共设施;另一方面“尝试诸如学习中国语言,派遣官方使节,乃至非法偷渡等各种进入中国内地的方法”。[6]在新上任的长官范礼安到来之前,这些工作都呈现出一种盲目和无序的状态。范礼安通过不懈努力、下功夫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他终于作为适应性传教策略的组织与策划者,使传教团进入到了中国内地。接手开辟新教区并检验适应性传教策略任务的,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罗明坚。他编写出《天圣教实录》,成为用中文编写天主教教义的第一位西洋传教士。但后来,他的行动有些冒进,引起一些麻烦,最终使他不得不离开在中国传教的岗位。罗明坚的传教活动,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适应性传教路线在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接替罗明坚的利玛窦成为了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集大成者,也成为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最耀眼的人物。在“适应性传教路线”的视角下,沈先生认为,利玛窦没有“神学理论家的偏执”,而是“宗教实践家的灵活”,他认为利玛窦“更关心的,还是如何根据西方神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在具体传教过程中取得明显成效的手段和方法”,“利玛窦及其后继者始终坚持和信守不渝的方针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民关心基督教。’”[7]获准能在北京居留后,利玛窦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及其观念,以及用中文撰写出《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等著作,希望士大夫们能接受天主教。而“利玛窦逝世后,朝中士大夫敦请万历皇帝钦赐坟茔的成功,乃可视为基督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的象征”。[8]
2
从人情世故看利玛窦传教的成功
关于利玛窦的生平及其传教过程,著述已众多,此书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在于,沈先生从细处入手,以《利玛窦书信集》为重要史料,对比罗明坚的失败,可以清晰地看出,利玛窦与罗马教会上层人士之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感情联系,为其传教成功提供了很大的助力。“我们知道,对长上需要像军人一样绝对服从,乃是耶稣会的基本纪律。将这个原则运用于中国的传教事业,那就意味着其传教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在中国的传教士能否卓有成效地工作,还取决于在澳门、果阿乃至罗马的长上对他们的作为是否理解、信任和支持。特别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新颖的方法受到其他方面责难时,情形就更是如此。”[9]
利玛窦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包括范礼安和阿桂委瓦在内的一些宗教上层人士,在罗马学院时就曾与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后经过利玛窦的不懈努力,遂与他们发展成为一种相当融洽和信任的上下级关系”,这些都为利玛窦后来“在中国别开生面的传教实践,提供了理想的人际关系,从而创造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10]利玛窦毫不掩饰他对范礼安的敬重,范礼安也尽可能地给利玛窦以关怀和照顾。“诸如将利玛窦调入中国教区,从肇庆撤离,该穿儒服,宽容中国礼仪,任命传教团监督,乃至晚年进入中国内地视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范礼安或是言听计从,为之担承责任;或是委以重任,放手让其施展才干。”[11]从《利玛窦书信集》中,还可看见利玛窦与耶稣会第五任总会长阿桂委瓦之间“灵犀相通、心心相印的情怀”。利玛窦总是“主动地写信,向这位最高长上表示诚挚的情感,并请求他的关怀和帮助”,并且,他“还经常汇报一些别人不愿触及、实则有关传教大局的敏感问题,甚至敢于就阿桂委瓦已发出的指示,提出修改建议”。“也许正是这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感动了阿桂委瓦,使得他对中国传教团的工作进展分外关注,也乐于向利玛窦提供各种帮助,并倾听和采纳他的一些建议。据此,沈先生认为,“正是通过建立在昔日师生情谊之上的良好的工作关系,才使本来距离最远亦最容易为人忘却和抛弃的传教地区,受到如此众多的高级教会人士的关注;亦使利玛窦这个原来‘生活在世界的边沿、外教人之间的一名无名会友’,越来越得到罗马长上们的垂青。这些来自罗马的关怀、慰问、鼓励和支持,显然是利玛窦在中国推行适应性传教路线和策略的极为有利的氛围与条件,同时也是抵挡其他教区人士对中国传教团的非议和攻讦的无形盾牌……正是通过这些利玛窦所说的‘这其中的玄妙是笔墨不易形容出来的’关系,成就了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12]
3
辩证地分析西学热潮代表人物的思想博弈
该书第九章论及“明末士大夫的西学热潮及其代表人物”,沈先生强调,“明末士大夫对西学感兴趣乃至形成热潮,主要是因为笃信西学与儒家学说深相契合,且可鼓吹、羽翼甚至隆懿儒学”。[13]书中以瞿汝夔为例说明“皈依基督教”是“明末社会动乱纲常隳坏的情况下,士大夫为寻求精神寄托和思想出路的一种表现形式”。[14]冯应京的事例,则反映出部分士大夫虽是“主动从西学中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灵沟通,直至深慕笃信其性命之学的思想进程”,却会因“娶妾”等问题而最终无法受洗入教。与冯应京同为朝廷官员的王徵,是受洗入教的士大夫之一,他“致力于基督教义与儒家相契合”。沈先生认为,“道德修养的吸引力和上帝信仰的归宿感”,在其皈依基督教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向往,及其指导下的科学实践活动”,则起到了巩固和促进的作用。[15]
关于明末士大夫受洗入教存在的思想障碍,沈先生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在难以理解如天主降生、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神学奥义,一在无法接受禁止娶妾的教规”。[16]前文所述的冯应京就因娶妾而至死未领洗,王徵也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被“除名教籍”,后来,他终割舍个人需求,并面呈铎德神父“悔罪书”,立誓悔罪,得到传教士的宽宥,重回教会的宗教生活。这是“传统孝道下的多妻制让位于西方教规的一妻制”,但后来,李自成攻克西安,王徵则但求速死以忠君报国,并不理睬自杀乃教规所不容,“在这里占主导的是士大夫的情怀,而非基督徒的诫谕”,这“反映了传统观念的压倒性优势”。[17]
沈先生辩证地看待这些西学热潮的代表人物,没有因为他们对西学的热心就将他们一切的行为都往西学上靠,更深层次地看到,耳濡目染的儒家教育,已经进入明末士大夫的思想深处。两种思想在头脑中的博弈,并不是一边倒的,而是或有胜负的,那么,针对具体的事例,就要具体的分析出到底是哪种思想的影响引出了这一决定。
4
关于徐光启与利玛窦的个案研究
该书第十章“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调适”,是一个关于本书“调适与会通”主旨的个案研究,交流的双方——明末士大夫的代表徐光启与传教士的代表利玛窦,分别作出调适中西文化的积极性的尝试。
之所以选取徐光启与利玛窦两人作为代表,沈先生认为,从利玛窦身上,“可以窥见西方文化那种精神传递或发散形态的特征,它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传统和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从徐光启身上,也可以“体察中华文明所固有的包容和融合的特性,并在他为引导传统文化走出困境而提出的‘会通’主张中,感受中华文化那种博大的胸怀”。[18]作者期望考察他们“在调适基督教义和儒家思想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采取的步骤、共同构筑的思想基础,乃至深远的意义”。[19]
沈先生认为,在调适与会通中西文化的整个过程中,徐光启心想事成,利玛窦则事与愿违。究其原因,沈先生认为,是“中国文化所固有的感染力,及其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和融合的特性”,“推动利玛窦调适活动从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突破认为设定的界限,以至于达到有悖于其母体文化价值取向”,这就使得在他的调适活动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相悖离的状况,即初衷是在于利用儒家‘这一教派的权威’来‘宣传天主的宗教’,而结果却变成了调整基督教义以顺应儒家传统价值”。徐光启的调适活动,“则是在主客观关系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将基督教义汇入儒家的思想范畴,通过前者对后者的认同、补充和纠谬,达到在新的基础上振兴传统的价值,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道德追求”。[20]
书中认为,“最能反映这种调适的性质和意义的还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他们特别重视的道德领域所共同构筑的思想基础……他们在符合良心的内在光明和自然法则,促使人们循规蹈矩、克服自身弱点和排遣外界诱惑,以及追求人类道德完善性方面,既是一致的,又可互为补充。”
沈先生对这二人的“有益的尝试”评价颇高。
三 读书后的一点疑问及想法
沈先生对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调试与会通的研究,其基调是,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主观愿望与客观事实相悖离,需要调整基督教义以适应儒家的传统价值;徐光启等明末士大夫的努力是求仁得仁,借用基督教真正达到“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的目标。在此,先回到该书的起始部分,看看“适应性传教路线”定义,“所谓适应性策略就在于,这些传教士‘准备放弃其偏爱祖传的西方风俗习惯的人类偏见,准备放弃基督教中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基督教附属的西方外部标记,但是不准备放弃基督教的本质。’”[21]若为了适应儒家的传统价值观而要调整基督教义,不放弃“基督教的本质”又从何谈起呢?利玛窦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怀鬼胎”的人呢?他是否真的“一会儿以该书曾斥责中国主要的宗教思想而自鸣得意,一会儿又深恐这些议论会开罪于中国官吏而惴惴不安”。[22]
读书后的感受,即是沈先生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厚的了解,且对其强大的包容性非常有信心;而在基督教方面,虽然他对于利玛窦等传教士有着详细的了解,但对他们所信的基督教义的了解则显稍弱,有些解释就不免让人疑惑。
如,在解读罗明坚的《天主实录》时,沈先生认为,“《天主实录》的内容,除了阐扬那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主宰的存在、特性及其相关的神学原理之外,便是将人世间的道德规范置于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符合基督教本质的。因为‘在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之中,道德完善性胜于上帝之其他一切显要的理智规定或理性规定’。‘基督教把道德造成了上帝,创造出道德的上帝。’而这种似乎是上帝所关切的道德的完善性,在《天主实录》中占有相当的篇幅。[23]用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认为的“基督教本质”去解释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罗明坚的思想,让人不得不产生时间错位的迷惑。
书的结尾处,沈先生认为,“倘若中国历史上这第二次(第一次为融化印度佛教)较大规模地对异质文化的接纳和融合过程,如不是因为罗马教廷的横加干涉而中断,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很可能不只是儒释道三教合流,而是在中国文明的包容下,儒基释道四教荟萃,融为一体的壮观场面。”当然,这是沈先生的美好设想,但不得不说,其实现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儒释道三者在中国文明的包容下可以合流,在于这三种文化中,没有一种是如基督教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徐光启诗所说,“立乾坤之主宰,肇人物之根宗。推之于前无使,引之于后无终”,[24]独一神的信仰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本质,若与三教合流在一起,接受儒释道中对天地万物、各路神仙的敬拜,这样所谓的“基督教”就不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基督教了。另外,三教合流在明末社会中的具体含义也有待考察,是指站在宗教立场上说三教一家,还是把三家的观念统一到一个新的宗教形态中,这二者是有根本性的差别的。明清之际,就有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它是由知识分子的学术团社演化而成的宗教组织,对当时的知识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徐光启也曾是三一教的门人。但是三一教也是被利玛窦作为“妖怪”加以批评的,所以徐光启在受洗入教之后,在其思想取向上抛弃三一教的理路。[25]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对信奉者思想上的要求,要比儒释道三教任何一种都要严苛的多,它要求信奉者认真思索分辨,不容混杂。明清之际思想的复杂性还有待更加全面且细致的分析,仅就徐光启而言,除了非常明显的儒耶思想的影响外,其对佛教、道教、三一教的态度极其思想演变的过程还需要更细致的梳理。
总之,沈先生避免了“一些中国学者所坚持认为的,仅仅是利、徐个人孤立的偶然的行为”,更不会“像当前某些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尽可用传教神学的‘普世性’和‘本土化’来涵盖其性质”,先生立足详实而丰富的史料,试图找到平衡之处,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大大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