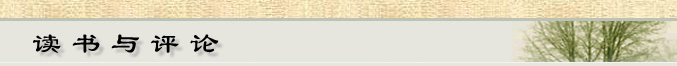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2012级硕士研究生
徐婷
【提要】孔飞力教授的《叫魂》一书通过讲述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及其背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故事和案情,在夹叙夹议中将事件中的普通百姓、官僚集团和“专制”君主乾隆皇帝的反应和行动,放进对传统中国政治运作和社会状况的思考中进行讨论,并分析了故事背后更深层的历史内涵。他的这种以小见大、自下而上、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分析政治事件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孔飞力;叫魂;1768年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Kuhn)199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通过研究中国帝制社会晚期的民众生活,来反观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的著作,荣获当年美国“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1998年陈兼与刘昶将其翻译为中文,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对看似偶然发生的社会事件“叫魂”一层层推演,从而构建了一个以“叫魂”为中心的一系列扑朔迷离案件的叙事,作者对其中蕴含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涵义进行了深刻分析,为我们理解“康乾盛世”为何成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1]提供了认识的途径。
一 全书结构以及内容
孔飞力在开篇讲述了四个稀奇古怪的故事,皆是发生在1768年与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相关的故事。叫魂,是一种“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的妖术。[2]因此,这些偶然事件竟很快演变成人们内心深处的巨大恐慌,事情也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发展开来。本来一个简单的社会事件却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地散播,开始并不为官府所注意,到后来竟逐渐蔓延到大半个中国。但是随着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对此事的关注,整个官僚阶层开始了在君主意旨下对“谋反”[3]事件的追查,(虽然在公开场合绝对禁止将“叫魂”中的剪发辫与谋反相互联系起来,)至此,开始了不断地大范围搜捕清剿。但是数月过后,竟然一无所获。叫魂恐惧最终被证明是一场杞人之忧的政治闹剧,乾隆皇帝下旨收兵,停止清剿。然而“盛世妖术”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统治阶级内部情况和当时社会深层状况、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内在的矛盾和危机却是值得深究的。
孔飞力在写作本书时,分别叙述了三个不同社会群体对1768年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在他对分别以社会底层民众、官僚集团和“专制”君主乾隆皇帝为主的三个故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晰在历史大叙事下更值得探析的政治文化内容。
首先是普通民众的情况。在多为人称道的所谓“太平盛世”的十八世纪,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陌生的妖术迷信及恐惧,会演变成为大范围的全社会恐慌?在孔飞力看来,满清王朝虽经过前代皇帝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到乾隆时达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但是透过这些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应。”[4]当时的社会状况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辉煌,乾隆时代只是“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罢了。人口的激增,出口扩大致使白银大量流入,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粮价因而上涨,产生了生存竞争等各种压力。因此在社会底层生存的普通民众的眼中,社会的种种状况还是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许多“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人们处在自身生存的焦虑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然而事情的表面下其实隐藏了更深层的内容,“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5]这反映出人们在“权力的幻觉”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同时也折射出普通大众权力极端匮乏的生存状态。笔者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公众自身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自我意识很容易被大环境所湮没,所存在的本能、潜意识其实已经不能再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了。其次是统治者的舆论操控,康雍乾时期的社会舆论控制始终保持一个非常严密的状态,因此大众自身掌握的信息不足,很容易受到统治者文化宣传的影响。而统治者的文化现象大都是其政治思想的表达,因而大众思维和行为就为统治者所引导和利用,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民众的一大悲哀。
其次是通过官僚阶级的所行而表现出的政治文化情况。孔飞力在书中对于官僚们在叫魂案中的态度也有深入地分析,作者认为,“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6]但是通过对清政府官僚和君主之间消息上传下达情况的了解,他发现在叫魂妖术发生之初的两个月,官僚们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捂盖子”的做法,竟然没有一个省级官员(无论满汉)主动向皇帝报告过妖术案情。经过作者的分析,这是因为在官僚君主制的社会制度中,“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一项罪行如果未经官方确认已经发生,那么,一个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惩罚”。[7]官僚们对于叫魂案发生的主要反应是及时进行处理,将妖术案扼杀在它的萌芽状态,让事情控制在自己所能管理的范围内,以此维持良好的治安。如此清政府各省的官僚对乾隆进行瞒报的行为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但是从中也看出在政府运行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官员们掩盖信息问题,这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危急中官僚们敷衍塞责的表现使皇帝越发愤怒和失望,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也令人堪忧。这也是后来乾隆皇帝利用叫魂案展开对官僚队伍整肃的原因之一。
最后是从“专制”君主乾隆皇帝的角度看的。孔飞力认为,清代的君主总是“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在常规方式和专制方式的统治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乾隆皇帝从在位初期起,“便对不起作用的规章条例表现得极不耐烦”,他“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他通过改变觐见制度、机要考评系统,以及把高级官员同常规制度部分地分离开来实现对官僚更有效的专制权力控制。针对叫魂危机,孔飞力认为,清朝作为满人入主中原,内心一直存在着猜疑和不安全感,乾隆皇帝对“叫魂”案的敏感,直接将它与谋反相联系的反应就是基于此产生的,他想借对妖术案件的处理,来进行满清统治的合法性声明。同时他对在叫魂危急中官僚们的表现极度不满,江南地区官员们的办事不利,强化了他一直以来对汉人官僚们从未消失过的猜忌。所以他认为要清剿妖术,首先要对官僚机器加以整肃。“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筒……已有的证据确实表明,当弘历看待官僚体制时,他的习惯用语产生于他内心最深层的忧虑,即常规化和汉化。”[8]
官僚机构“常规化”的权力,是指在官僚君主制下,依据已经确立的制度或规章条例,政府机构能够正常运行,各级官吏也能按部就班地行使的权力。一般以常规化权力运行日久的政府,很容易变得千篇一律因循守旧。正如在“叫魂”案件中,官员们为了自己的私心“捂盖子”,严重缺乏行政效率和处理问题的积极性。对于官僚的常规权力和君主的专断权力之间的关系,孔飞力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官僚的常规权力和君主的专断权力这两种权力是可以和平共处的。[9]君主通过“政治罪”的概念,把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解决的特殊事件,收归自己直接管理,进行直接的命令,清理他的官僚队伍,以此强化他对于官僚机器的控制。如此可使专制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君主的专制权力达到了更高的程度。因而“叫魂”事件实际给乾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官僚系统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展开对叫魂案的清剿,君主再依据官员们的表现确定赏罚,从而强化了他对官僚的控制,使君主的专制权力达到顶峰。
对于“汉化”的问题。孔飞力从满清帝国“合法性”构建及维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满人对于要吸收精湛的汉人文化和保持满人本性之间的矛盾态度。大清帝国到了乾隆时期,看似已经很巩固了,达到了所谓“盛世”的局面。但是满清统治者内在的少数民族背景,却使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放心过,因而一直存在着“合法性焦虑”。[10]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一如既往的“焦虑”并不是过分敏感所致,在清末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腐朽之时,用来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且对于激励民众加入讨伐满清的队伍还颇具吸引力,所以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
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 关于本书的研究视角
有关《叫魂》一书的研究视角,历来有不少学者对此加以讨论。一般而言,多半是主张这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新政治史著作,
认为《叫魂》一书注重从普通事件中找出问题,不再局限于描述历史,而是分析和解释历史。该书“置政治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分析,是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是一种新的政治史”,
“是一种总体史观和从下往上看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的政治研究”。[11]孔飞力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到了历史研究中,以此解构传统的政治史,用社会史视角来讨论政治意义,实现了自下而上看待历史。故多半学者认为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选材和分析角度,给历史研究或是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还有学者将《叫魂》视为一部社会分析的社会学著作。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叫魂》是通过对中国近代前夜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分析来解释近代中国‘悲剧’命运的,这样的分析符合社会学通过分析社会行动的意义,从而达到对行动的理解的解释模式”。[12]社会学研究是通过对人们的行为、关系、态度及由此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产物的科学探究,进而理解世界、预测社会发展、变迁趋势。《叫魂》一书正是通过对叫魂案的回顾,分析它如何从一起简单寻常的社会事件转化为政治事件,并通过描述和分析清代社会的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的消长及官僚君主制实际运作等政治情况,来理解为何在“盛世”光环笼罩的时代,叫魂事件会成为中国悲剧性近代“预示性的惊颤”。[13]
还有一部分人类学学者将《叫魂》一书当做历史人类学著作。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就是以物为中心来叙述和分析历史,“通过从物的历史中解读和推测出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结构关系的变化”
。[14]他们认为在《叫魂》一书中“头发”是全书的关键,在文化中有诸多象征意义,它引发出之后一系列故事的叙述以及对政治运作情况的讨论。“叫魂中的发辫,它关涉到文化性、政治象征性、妖术性以及这些多重性的含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相互交织而构成的矛盾,因而提供给我们一个复线的、并相互交错关联和作用的历史过程。这种研究视角,是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之一”。[15]
作者把产生“盛世妖术”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背景情况展示于读者面前,分别讲述了普通民众何以在“盛世”的局面中对“叫魂”妖术产生如此大的恐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权力幻觉;清朝官僚们在事件中表现出的行动迟缓和态度怠惰及其原因,以及帝国的上下级通信问题;皇帝对其统治合法性的焦虑及对官僚君主制中存在的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因此它是一部社会史研究。而孔飞力以“叫魂”案为线索展现了社会各阶层对于叫魂妖术的不同解释和行为,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解释和行为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从一件发生于民间的叫魂巫术事件中解读政治体制,因而它也是一部政治史。因此笔者认为《叫魂》一书是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是一部从社会史的研究角度来分析政治意义的历史学著作。
三
需要注意的地方
孔飞力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59—1964),曾师从费正清学习中国近代史,后在1978年秋重新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虽然在学术和工作上都与费正清有密切的师承关系,但是在对待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问题上,二人有着显著的差异。费正清主张中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缓慢地从传统走向近代,即“冲击—反应”模式,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内聚力和结构坚强且稳固,而国内变革力量弱小,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对西方威胁作出迅速的反应,[16]想要获得发展,只有借助外来的冲击。可以看出,费正清将中国近代变革的根本原因归于西方冲击,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的冲击确实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影响巨大,但是外因必定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费正清的“西方中心论”过于夸大了西方冲击的作用;孔飞力是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其第一部专著《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1970年出版,与其老师的研究思路完全相反,他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中,倡导“中国中心观”。在《叫魂》一书中,他试图通过叫魂案件,透视整个清王朝对社会的控制,这是从中国内部事件去看所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情况,从中国社会内部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他的“中国中心观”在《叫魂》一书中得到显著地体现,我们在分析该书时也要注意这个学术研究转向上的表现,才能更容易理解孔飞力在《叫魂》这本书中讨论的深层涵义。
孔飞力《叫魂》一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一次社会上流行的巫术恐慌,以及由此产生的叫魂案的审理过程,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孔飞力列举的与妖术相关的事件和案情,多取自《录副奏折》、《朱批奏折》、县志等原始的手写档案,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实为不易,值得敬佩。但其对案件背景的还原也大都是用当时人的一般性记录(如在各种奏折、地方志中找出的与妖术有关的案件)和现代人的普遍性研究(如通过卜德的著作《十八世纪北京的监狱生活》来还原其书中对妖案犯人的惩处情节)来进行的,因而在孔飞力的著作中,其对案件过程过分细致如临其境地描写,多是依据这些材料进行想象和揣测的结果。在清朝的《大清律例》中,并没有关于“叫魂”之罪的具体条款,孔飞力所用到的律例规定是对原本广泛含义中处理巫术、邪术条例的类比和套用,也没有直接的材料表明乾隆三十三年的这场妖术恐慌,确实成为全国范围内、波及政治等级两端的政治事件。
但孔飞力却将剪人发辫这样普遍流行于中国的巫术同谋反结合起来,他认为乾隆皇帝从他自身的不安全感出发,自然地将叫魂案件中剪人发辫的现象同清初的剃发令结合起来,进而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扩大,将其提升为事关谋反的政治罪,并加以利用来大规模整治官僚系统,以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这种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真正发生于历史的妖术事件未必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因为目前我们无法从清朝一代的历史记录中找出乾隆皇帝在其主观考虑中,清楚地意识到要扩大割辫叫魂案,用它来整肃官僚机构的证据和事实。“《叫魂》一书的瑕疵可能依然在于它注意了特殊的时事,而比较忽视平时的寻常,而这正是传统政治史的不散阴魂。”[17]因此孔飞力的分析,与其说是论断,不如说是假说。
在我们专门研究某一事件或试图回答某一问题时,容易过分强调特定问题的重要性,有时未免有夸大意义和虚构内容之嫌,这在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应当予以重视。但是对于《叫魂》一书,作者多有创见、文笔生动,以及从社会史视角下研究政治史的研究范式等优秀之处,仍值得我们拜读并认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