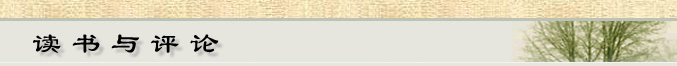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
评《明清社会史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13级博士研究生 石路遥
[提要]已故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巨著,作者详细考察明清两代上万名进士履历和多重史料,认为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有巨大促进作用。何氏对精英和社会阶层流动问题既有深刻的学理研究也有个人家族切身体会。这本书是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之一,时隔半个世纪重读这部作品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科举制度;社会阶层流动;社会史
一 其人与其书
著名华裔史学家何炳棣在美溘然长逝,留下等身之著作驾鹤西去,令学界后辈哀思不已。何炳棣先生先修化学后转入史学专业,考取留美官费西洋史门,在哥伦比亚大学以研究19世纪英国土地改革与国家政策而获取博士学位。上世纪中期,能进入美国学术圈成为一流学者的华人寥寥可数,而何炳棣就是这样的先行者。另一位华裔史学家余英时评论他“才大如海”拥有“万丈豪情”,此论绝非过誉。
何先生平生治史注重选题,自身背景知识结构注定了他能够出入史料游刃有余,又能综合西人治史之专长,并将中国历史背景同更广泛的西方历史进程两相对比。这位性格刚直奇崛,一生都在战斗的学者,晚年因《读史阅世六十年》而闻名华语文化界,但史学圈对他的了解却早已从其更为重要的学术研究开始。他为史学界内部所熟悉的研究如人口史、会馆史、以及退休后的思想史攻坚等等皆有中译本或国内发行版。而他对社会阶层流动和科举研究影响甚巨之《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直到2013年才由台湾徐泓教授精译为《明清社会史论》,
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时隔半个世纪让我们再来研读并审视这部给教育学界、史学界、社会学界都带来重大影响的学术作品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相较于其它研究,何炳棣在讨论社会阶层流动问题时比旁人更多一分切身体会。何氏一门三杰何炳松、何德奎、何炳棣,皆是当时沐欧风美雨的杰出精英。但是在浮华背后不得不面对的是曾经亲老家衰的迫切压力。何父年轻时亦为廪生,科举废除后转习日文及政法,曾在家乡创办现代小学,却被乡里旧派人物不容,最后被迫离家、愤然北上。家道中落的经济压力、壮志未酬之失落、和年近半百才得一子的各种焦虑……这些始自父辈的种种焦灼投射到何炳棣的身上,使他自幼已经知悉必须努力奋斗出洋留学才能成功登上社会成功的阶梯。
自年少时代起何炳棣不得不身负重整家庭地位的使命。而其父认定改变命运的办法之一就是在新时代的洋科举中脱颖而出。事实也的确如此。何父无力资助儿子自费出洋留学,自年少起何炳棣就不得不期望考取留美官费留学生。在这一目标下,他原本研习化学,但数理基础很弱导致他难以达到拔尖。终于转入历史后,随之面临第一次留美考试名落孙山、国难当头大学南迁、史学门出国留学资助项目差一点被取消……最后通过考试层层选拔才终于战胜同辈竞争者,获得唯一的一个历史学出国名额。何炳棣晚年回忆总角之交诗人朱英诞对“命运注定必须投考新科举”的他从不视为庸俗功利,并且深深懂得他少年时代即使在最懵懂贪玩时内心始终隐藏着一丝永远的阴霾。
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家族前途的不安全感使一位青年渴求成功,为了获取这希望渺茫的机会,经历长达十多年的准备、等待、挫折,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次次面对失败。这些经历背景塑造了何氏性格奇崛,脾气急躁的一面。徐泓先生说他为人率真、不假颜色以至于很多人怕他。[1]几年前几乎与《读史阅世六十年》前后相继出版的另外一本《上学记》中,学者何兆武曾经回忆初入西南联大时去历史系图书馆借书,何炳棣对他们这些低年级学生很凶,“盛气凌人”且“目的性太强”,一生读书功利,一心想要考新科举出国留洋。[2]何炳棣晚年亦自诉其一生难以和中外学人和平相处,实乃性格之失。从这一侧面我们也能理解何氏对于科举和社会流动问题的关注有着更多的切身体会。
该书中文译者徐泓先生为明史研究专家,他与原著者何炳棣先生有着长达数十年的深厚渊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徐先生撰写硕士论文《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与博士论文《明代的盐法》时便受到何炳棣关于盐商和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的部分影响。此后四十多年教研工作中也屡屡接触相近历史时段和相关史料。在翻译的过程中,徐泓先生又多番与何炳棣先生反复讨论,补正相关资料。
阅读中文译本时每每惊讶于译者能一一查对何炳棣原书所依据的文献,重新核实何先生的一些细微的统计错误。由于相隔半个世纪,资料和信息检索的迅猛发展使得今人拥有的条件远较何先生撰书之年更为便捷美备,不少领域已有新发展,史料也有新发现。译者在底注之中对相关学术动态亦有进一步介绍。长达万言的译者序,不但是对何先生一生治学概要的总结,也同时是相关议题之学术史。可以说由这样一位明史专家做的精良译本对学生后辈实在是施惠甚深。
二 本书内容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
出版于1962年,此后何先生根据新增资料局部修订并于1967年再版,本次译本以第二版为主,全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分层化》
:作者在一开始将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勾连起来,详细分析了中国历史上诸种贤才观念和人才选拔制度。他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那种平等观念,先秦儒、墨、法诸家认为社会不平等和分割是理所当然且具有正当性的。至汉代各思想流派对于贤能的标准不一反应在选官标准的多样化。由于汉代察举制对人才贤能的定义较为宽泛,对于贤才选择缺乏可执行的统一标准,此制逐渐沦为世家大族延续自己家族势力的工具。察举制以后有九品中正制,其曰“中正”本为公正不偏,但很快也被滥用为“依据候选人家庭地位而定”。此后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继续垄断社会阶层。直到隋唐开始设立一定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施行六科取士。此后六科取士从最初的“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和进士”六科收缩为对于经书的记诵。虽然唐以后对于贤才的认定更为狭窄,但这样的考试确实增加了可够评议的客观性。这也是进士科能长期存于中国的原因。在第二节作者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之分实际上并不是严格的社会阶层区隔,传统社会是一个多元阶级社会(multi-class
society),社会阶层由社会威望、接近权力的程度、财富、教育等各方面因素决定。通过详细考察盐商的具体个案和明清小说等资料反应的社会世情,作者指出明清时代财富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权力,必须通过“入仕”转化成官员身份。因教育意味着为官机会,无形中使得教育具有对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于是传统中国逐渐形成重视读书应考的社会理念。
第二章《社会身份制度的流动性》作者认为尽管明承元制采用世袭的身份户籍制度,但却并不能永久冻结社会阶层的变动。作者考察明代户籍登记制度,以“军”、“匠”、“灶”三种特殊劳役身份的变迁历史为例,为我们揭示十五世纪以降工匠逃役、军户逃籍、盐户破产分化,世袭身份制度随着时间流逝最后都被破坏的历史事实,这也可以从特殊身份进士和明清小说的例子中得到验证。作者用明代特殊身份进士的例子做旁证,通过统计分析揭示明代职业流动导致大量身份流动。第三节以更广泛的社会文学、族谱和传记为史料,继续揭示法理上对于职业流动的限制逐渐只是空文。作者从法理上和社会实践方面揭示明清两代对身份流动并无绝对限定。与此同时,在复杂社会面相的背后,相对单一的儒家贤才观念借由多重管道(宗族、家庭制度等)广泛渗透到各个阶层为不同社会群体所接受。
第三章《向上流动:进入仕途》中作者将“进士身份”作为国家精英的严格定义,使用上万名进士履历材料为基本史料。他将史料中的举人分为四类,A类是祖宗三代未有一人获得过初阶科名的生员,B类是祖宗三代之内产生过一位或者更多的生员但未获得过高阶功名,C类则是来自于祖宗三代之内有过一位或者更多获得高阶功名,其中C类下再划分一个子类D类:其祖宗三代有三品以上高官,属于绝对的特权精英家庭。经过作者统计整个明清时期A类和B类举子共占42.7%,除了顺治十二年、康熙十五年、二十一年、四十二年四次科考以外,出身高官家庭的进士从未超过10%,而D类进士平均百分比甚至仅有5.7%。可见科举考试在明清时代有效维持了社会流动。同时对明清时代后期的史料统计还可以发现,A类进士人数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清代末年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放在社会脉络中来看即是说寒门出生的人士爬升社会-官僚体系的阶梯困难和挫折越来越大。
第四章《向下流动》主要使用家谱这样一种资料。明清时代宗族并非每个地区均衡发展的组织现象,此外家谱并不记载一般家族大部分成员的社会、职业与经济地位等相关信息。因此在这一章难以使用统计量化对比的手法,作者转以王士祯家族、桐城张氏、无锡嵇氏与海宁陈氏这四个家族个案为实例说明社会分层化的普遍过程。在这一章中作者进一步想要论证的是:中国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即使是最显赫的家族,其子孙后代如果不能成功地通过科考获得功名,也无法阻止他们逐渐下沉的社会命运。这与18世纪英国几百个家族长期垄断社会政治权力的情形呈强烈对比。导致家族向下流动的原因,部分由于世家大族逐渐发展出一种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雅者寄情文学、书画,或粗鄙者挥霍家财,以至于家族财富逐渐减少。也有部分原因由于家庭制度,没有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儿子们平等享有分家析产的权利也使得大家族财产逐渐分化。
接下来在第五章《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中,作者分析了与社会流动相关的所有其它因素。明清两代对进士名额严格管控,官学学额呈现逐渐冻结、不能与人口增长同步匹配的情况,使得平民阶层向上流动的阻力变大。在地方中下层社会承担基础教育功能的是社学,随着明中后期社学衰退,私人义学和书院逐渐兴盛。到清代书院从明代的自由讲学研究导向逐渐转为科举应试为主要目的。此外还有各种辅助正式教育的民间管道,如各种地方性社区义学、贡士庄等等,以及各省地区在京新建的专供地方子弟赴京赶考使用的会馆。这些现象的存在不能算提高地区流动的因素,但这种现象至少反映地方社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地方子弟取得科举和社会名望的心理事实。宗族组织也对族人的社会阶层流动具有一定影响。明清时期刻书出版业的繁荣一方面使得知识文化再度向平民扩散,但这并不意味着下层寒素之士更容易向上流动,因为书籍增加的同时也可能是贫富教育资源不断悬殊化的时代。此外,战争与社会动乱、人口与经济因素也会干扰社会流动。
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作者融汇在此之前所做的明清以降人口问题的研究基础,从进士的地理分布及地域社会流动率的变化入手分析。随着中国人口、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在明朝立国以前北方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已经十分明显。而浙江、江西、福建、江苏等省逐渐在科举中占据优势。对此明代皇帝按大区配额的形式固定分配进士名额,到清代康熙五十一年分省定额制度,无疑使得南方科举强省吃亏而北方相对受益。从地域流动差异上看明代文化和社会活力主要源于东南,相比之下北方和长江中上游及西南诸省社会流动率相对较低。但进入清代以后,前述定义的A类进士在东南省份比例却急速下降。相对于其它地区,在东南经济文化强省内寒微之士向上流动的竞争越来越大。此外科举强盛地区因经济实力的变迁,也并不能一直保持优势,逐渐存在地区间优势此消彼长相互流动的局面。
最后第七章《概括与结论》作者总结认为传统中国的竞争性科举考试制度作为国家选拔官僚流动的重要途径,远比产业革命与国家义务教育制度建立之前的西方社会更胜一筹。但这套制度也由于突出单一意识形态价值、考选内容固化,导致对其它知识系统和实业技术的轻视。而后者恰恰在西方社会内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受到社会尊重,并最终促进西方世界不断翻转发展。
三 研究方法及其它
何先生在完成本书之前已经出版《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3]亦有涉及两淮盐商的数篇研究性文章,此外作者曾专修数种分析工具。这样一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求学背景使得他有能力也有眼光出入西洋史学和中国史料,将“中西两种文化处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之处。[4]
1960年代有两种史学范式正在欧美兴起: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社会史和运用统计计量的史学。[5]主流评论认为何炳棣的成功在于成功引入社会学视角和统计方法。事实上通观全书作者运用的统计方法并不复杂,基本是简单归类和计算。何氏运用资料也非常小心,比如在讨论“向上流动”时以上万进士履历为基本材料,可以做简单的分类统计。但在处理“向下流动”时限于客观情况不可能运用同类方法就不用。
再论社会学视角的引入。传统中国学术对于阶级、性別和种族等议题可能较为陌生,但在196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运动的方兴未艾,这些社会辩论的焦点问题也成为美国学术界的重要的议题
。特别是这本书处理的核心问题“社会阶层流动”、“社会分层”等涉及社会学科对于社会历史的特定视角。在社会学领域,最早提出阶级问题的马克思就主张阶级/阶层是一个历史范畴,应该把相关分析放置在特定的时空架构里具体研究。韦伯曾经也提出“权力、声望、财富”等三向度的社会层化理论,还有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等等。可以说阶级/阶层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分层和阶层流动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科的核心热点议题。
何氏撰写本书时就直接借鉴过社会学的方法。在社会学理论视野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Bernard
Barber提醒何炳棣注意彼时社会学界研究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正转向“opportunity
structure”这一概念。[6]何先生将Opportunity
structure译为“机缘结构”,这个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提出,指的是与一定地位、角色相联系的机会资源,它决定着人们的努力能否获得回报。[7]该书第五章讨论各种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其背后的核心理念即受启发于此。
何炳棣撰写的中文译著序言中强调,这本明清社会史是他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较多的作品,引发了不少后辈效仿。但此书问世若干年以后作者对某些社会学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很少有著作能够把论述放在收集到必要数量和多种类型的坚实史料的基础之上。这样就不免流于削历史之足适理论之履的境地。
《明清社会史论》提及与张仲礼先生关于中国乡绅精英定义的不同意见,认为后者过于宽泛和语义模糊地使用了“绅士”和“gentry”这两个词汇。何先生熟悉英国历史,他提到英文“gentry”一词从英国Tudor王朝以来一直具有特定的意涵,在17-19世纪这个词尤其是指经济方面坐拥庞大地产、政治方面能控制并支配“郡”的十分特定的群体。而“绅士”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绅”指缙绅、乡绅、乡官、乡宦等官员,包括在任的或者退休的、候补的;而“士”或“缙”则专指学者,尤其是未出仕任官的学者。而且在中国传统里,决定“绅士”地位的是科举功名而很少由于财产因素。在这里何炳棣先生提出的一种方法论的视野值得我们借鉴。他尤其提出“在一定限度内,我们当然可以借用一个外国名词,但当被借用的名词所产生的环境,和原来的社会经济政治脉络,离我们太远时,我们就有强烈的理由完全拒绝这个名词。”[8]
何炳棣对韩明士(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书的批评也集中在两点:1,对家族、宗族等概念范畴定义松散含混不清,将同姓同乡之人随意认定为“同族”,事实上家族的官方或世俗标准是“五服之内的血缘组织”;对“精英”一词的任意滥用,举凡官员、乡贡、地方捐献、造桥、渡船者都属于“精英”,这就无形中扩大了精英家族的范围,降低科举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促进作用。2,史料有限。何炳棣专书引用了一万四五千份进士履历,且辅以大量族谱、传记、小说等等史料,而韩明士仅集中于抚州地区。
欧美史学界在80年代左右出现的新文化史便是对60年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式的一种逆动。原有的被社会结构化-功能化的讨论被重新认识,特别是对范畴化的那些概念本身进行分析。例如前文提及“阶级”本是六十年代社会史的核心议题之一,新文化史学界开始反思划分“阶级”范畴本身时发生的简单化和归类化。而从以上两点讨论折射出何先生一生治史之眼光。他的学术生涯伴随着社会-经济史范式的兴起,但何先生并没有沦为简单使用范式理论的奴隶。一些后世才意识到的范畴化分类问题,何先生已经注意到了。
何先生一直认为治史应该理论和资料并重,传统西方汉学界的研究和视野过于专狭琐碎。尽管《明清社会史》一书是他运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学界热门课题的著作,但何氏最为出彩的还是在于他能大量运用、考订、诠释多种史料。这不失为“史家养命之源,岂能弃之若敝履”。[9]
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史学。一种潮流的变动,并不是将前者的功绩全部否定,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以及继续吸取社会史成功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以及部分史料的解禁和新信息时代带来的资料的交流,多重侧面多重维度看历史,势必可以将史学工作进一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