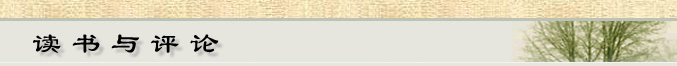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
《普鲁塔克与罗马》述评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2012级博士研究生 张元伟
【提要】C.
P.
琼斯的《普鲁塔克与罗马》一书是普鲁塔克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以普鲁塔克的存世著作为基础,结合“第二次智术师浪潮”这一社会思潮,详尽阐释了普鲁塔克与罗马的关系及其对罗马的态度,从侧面考察了罗马帝国初期希腊罗马文化高度融合这一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书中所使用的“人物关系志”等研究方法,对著作家生平经历、史料别裁和撰述目的等主题的精到分析对后继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书中有些观点也存在夸大、误读史料的问题,尚需读者引戒。
【关键词】普鲁塔克
罗马 第二代智术师 文化
传记史家普鲁塔克历来是古典学术研究中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自二十世纪中叶逐渐摆脱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史学思潮的窠臼以来,普鲁塔克研究在西方学界更是掀起热潮,研究视角和方法不断出新,探讨的主题逐渐丰富,名家佳作迭出,成就蔚为壮观。国内学界对普鲁塔克的提及盖始自梁启超先生,[1]但多年来关注较少,直至近年陆续出现一些探讨其史学思想的论著。应当说国内学界的普鲁塔克研究尚蹒跚起步,作为初学者或研究者,当下除了应加强对原典文献的释读外,还需对西方的研究理路做系统的梳理了解,而琼斯的《普鲁塔克与罗马》[2]便是这样一本了解研究普鲁塔克需仔细品读的经典佳作。
《普鲁塔克和罗马》一书由作者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扩充而成,于197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导言、附录、参考书目和索引外,正文分两篇十三章讨论普鲁塔克与罗马的关系。上篇六章详述普鲁塔克的生平经历,下篇七章以普鲁塔克存世著作为基础,分析其对罗马的态度。概言之,从著作家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出发考察其著作和思想,以及对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治下希腊罗马文化已融为一体这一整体文化社会环境的认同,是作者在本书中所秉持的基本理路。至作者成书时期,这种范式在罗马帝国史研究中已非鲜见,作者也承认该书的写作深受前贤影响,如R.
Syme,F.
Millar,以及G.
W. Bowersock等。(前言p.6)然而于普鲁塔克研究而言,此种视角的考察却有开创性意义,作者在书中所论及的问题,举凡著作家本人的生涯社交,其撰述方法、材料取舍和撰写目的等,都对后继者有重要影响。
一
该书上篇六章中对普鲁塔克生平的介绍,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普鲁塔克的家世背景,普鲁塔克的学术和政治生涯,普鲁塔克的社交。
第1章论述普鲁塔克的出生地凯洛奈亚(Chaeronea)及其家世。普鲁塔克出生于军事重镇凯洛奈亚一个上层显贵家庭,并在此地度过大部分人生岁月。在当时希腊学人竞相前往罗马求取功名的风潮下,普鲁塔克的才学名望和他对家乡的眷恋使作者深信,“探讨普鲁塔克与罗马的关系需从探讨其于凯洛奈亚的关系开始。”(p.2)凯洛奈亚所处的地利之便使其成为兵家要地和彼奥提亚(Boeotia)地区首屈一指的城市,在作者看来,显赫的家世背景使普鲁塔克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步入当地政坛,同时也使他得以结交其它城市的显贵,其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祭司一职的获得便与此有莫大关联。(p.10)然而,作者同时认为,家世背景对普鲁塔克的影响不应过于夸大,虽然家庭背景和财富使其身居社会上层,但其后来的社交范围,尤其是和罗马显贵的结交却远非家庭环境所能给予,罗马公民身份的获得更是著作家个人能力的体现。(p.11)
第2-4章论及普鲁塔克的生涯。由于著作家本人并未有自传留世,其生卒年月和生平经历多由现存著作中的零星记载推断而来。作者据此按时间顺序将其生平划分为少年求学、中年思想成熟以及晚年创作盛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罗马皇帝尼禄,弗拉维王朝以及“五贤帝”初期三个时段。(p.13)在尼禄治下,普鲁塔克求学于雅典学园,初研习数学,后接受修辞学训练并曾游学“第二代智术师浪潮”(the
Second Sophistic)的发源地斯米尔纳(Smyrna)以及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等地,在尼禄统治末期将兴趣转向哲学,并由此奠定以后的思想生涯。在此期间普鲁塔克曾被选派为凯洛奈亚使者谒见罗马帝国阿凯亚行省(Achaea)的代执政官(Proconsul),尽管此事的确切时间尚待考订,但作者认为此或许为“普鲁塔克第一次和罗马统治阶层的交流”。(p.16)
弗拉维王朝统治时期是普鲁塔克与罗马联系的活跃阶段。普鲁塔克曾多次到访罗马和意大利,期间多有公务和讲学。然而普鲁塔克于其中细节三缄其口,未有明确记载。关于造访时间,作者据散见于其著作中的零星关联事件推定出三次:苇伯芗(Vespacian)统治期间一次,图密善(Domitian)统治期间两次。(p.21-24)关于造访身份,鉴于此阶段普鲁塔克已获得罗马公民权,与索西乌斯·塞奈西奥(Socius
Senecio)等罗马政要显贵结识,成为凯洛奈亚当地的政要,并担任德尔菲两位祭司长之一,作者推测他可能代表凯洛奈亚、雅典或德尔菲等多重身份。对于普鲁塔克此种缄默态度,作者认为“并不能因为其不曾述及而推断他在政治上的微不足道。”(p.21)而关于此阶段普鲁塔克的少产(仅有几篇散论和《帝王传集》[Lives
of Caesars]),作者认为这与此间公务繁忙以及图密善对哲学家的迫害而致的“禁声”环境有关,而著作家本人对于弗拉维王朝三位皇帝的态度,也充满否定和敌意。(p.25)
“五贤帝”初期从皇帝内尔瓦(Nerva)到哈德良(Hadrian)统治初普鲁塔克离世这一时段,作者认为是著作家声明和创作的盛期。普鲁塔克被皇帝图拉真(Trajan)授予“执政官荣誉”(consularia
ornamenta),并在皇帝哈德良继任初被任命为阿凯亚行省监守使(Procurator
of Achaea)。[3]普鲁塔克大部分传世著作都在此间完成,其中包括《对饮集》(Table
Talks)和享誉后世的《对传集》(Parallel
Lives)。作者将普鲁塔克与同时代的哲学家普鲁萨的狄奥(Dio
of Prusa),爱彼克泰图斯(Epictetus),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polonius
of Tyana)相比,认为虽然普氏与后三者在出身、阶层、学说主张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站在‘第二代智术师浪潮’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前沿。”(p.37)而且,“普鲁塔克的生涯在诸多方面都是希腊文人志士不断投身罗马帝国政界和社会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p.38)
第5-6章作者着意探讨的是普鲁塔克的社交圈。依据于普鲁塔克本人和其他著作家现存著作的相关记载,作者以帝国不同时期普鲁塔克所处的身份地位和政治环境(主要是尼禄、图密善和图拉真统治时期)为经纬仔细介绍了著作家的社交对象及其相互关联,构建出详尽清晰的社交网络。作者反对将著作家的交往对象划分为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这种划分极其危险”,因为“就法律身份而言,普鲁塔克及其很多希腊朋友都是罗马公民,而很多在罗马担任公职的朋友都来自希腊语地区。”(p.39)因此他以地域为界来探讨梳理:第5章述及本土社会(Domi
Nobiles),第6章探讨位于西部的罗马帝国(Rome
and the West)。
二
下篇七章内容作者立足于对普鲁塔克现存著作的归纳分析,探讨其对罗马的态度。第7-12章按类型和写成时间述及四类著作,最后一章总括普鲁塔克对罗马的态度。
第7章论及普鲁塔克早期的历史演说词。作者认为对于这些早期接受修辞学训练时的习作,“于其鲜明撰写目的的过度期待是不明智的,有益的尝试在于界定其目的,并且消除对普鲁塔克年轻时政治思想的误解。”(p.67)在《论罗马的幸运》(De
fortuna Romanorum)一篇中,普鲁塔克不同于其他希腊著作家对罗马成就的敌意见解,认为罗马的幸运“不仅在于善把握机会,更归功于美德”,作者认为普鲁塔克此举“本身虽不是对罗马的正式颂扬,但也绝不是攻击”。(p.68)虽然该篇末普鲁塔克认为罗马的幸运也归功于亚历山大的早逝,但作者认为这绝非著作家对罗马的敌意,因为他在罗马派使者前往巴比伦谒见亚历山大一事的缄默态度与李维和其他罗马史家保持一致。作者强调:虽然《论罗马的幸运》并不能代表著作家本人的政治信仰,但罗马的幸运是结合了神意与美德的观念对普鲁塔克颇有影响,并出现在后期的作品中。这些观念虽承袭自史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但反映着作者的个人信念。该篇演说词中认为“罗马是风暴和波折中的铁锚,是混乱世界中稳定因素”的观念更是帝国治下普鲁塔克和其他著作家的普遍认识。(p.70)而另外两篇演说词《论亚历山大的幸运》(De
fortuna Alexandri)和《论雅典的荣耀》(De
gloria Atheniensium)中,著作家同样将亚历山大和雅典成就归因于美德和幸运的事实表明,这些著作家早期的作品中的观念,已初露其成熟时期思想的端倪。(p.71)
第8章作者论及普鲁塔克的传记作品《帝王传集》(Lives
of Caesars)。该单传集以从奥古斯都(Augustus)到“四帝之年”最后一位皇帝维特利乌斯(Vitellius)为立传对象,现仅存《伽尔巴》(Galba)和《奥托》(Otho)两传。作者推定其成书时间应在皇帝图密善统治时期。(p.73)就传记特点而言,作者将普鲁塔克与同时期《罗马十二帝王传》(Lives
of Twelve Caesar)的作者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相比,认为后者多着意于对事实的清晰记述,而普鲁塔克则承袭波利比乌斯关于历史和传记的观念,更倾向于有选择的叙述重要事实以凸显帝王的性格,这种道德关注和伦理兴趣与后期作品《对传集》中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p.72-73)就材料运用而言,传统观点认为普鲁塔克在这两篇传记中的取材与塔西佗(Tacitus)的相关记载基于同一位作品未传世的罗马史家,但作者反对此说,认为两位著作家对于同一事实的呈现和安排不同,普鲁塔克对材料的获得可能是通过罗马密友的口述提及而非成文作品,而且普鲁塔克的拉丁语水平在撰写该传记时尚未达到如此水平。(p.77)尽管《帝王传集》仅存两篇,但作者认为这两篇不失其典型性,普鲁塔克的撰写兴趣在于人物的性格刻画,虽然其中并非不述及政治,但这一单传集的写作目的是非政治性的。(p.80)
第9-11章作者概述普鲁塔克名扬后世的传记作品《对传集》(Parallel
Lives),[4]论及其史料别裁和撰述方法(第9章),其对罗马历史的看法(第10章),以及撰写目的(第11章)。由于《对传集》中所立传的人物有一半是罗马人,著作家的拉丁语水平,以及其对拉丁语史料的使用再次成为作者在第9章中探讨的焦点。基于《德摩斯梯尼传》(Demosthenes)开篇著作家曾自述造访罗马期间因公务和讲学繁忙而无暇练习拉丁语,但在著作中又大量使用拉丁语材料的事实,作者认为其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而矛盾的解决需立足于普鲁塔克的写作背景和当时的写作传统,即普鲁塔克可与说希腊语的罗马密友交谈而获得资料,亦可借助于专业的奴隶翻译匠翻译拉丁史料。再者,当时宽松自由的引述风格也使著作家不必拘泥于精确的引述。(p.82-84)作者同时强调,普鲁塔克对这些假借他人之手的材料运用并非是对他人观点的复制和拼接,而是服务于其刻画性格的主旨和写作目的,这体现的是普鲁塔克本人对罗马的态度。(p.87)
至普鲁塔克时期,传记作为一种写作体裁已趋成熟,著作家的叙述和选材自然体现其观点和倾向,因此在第10章中,作者主要选取罗慕路斯的统治,罗马对希腊的干预,以及罗马共和制的衰落这三个主题来分析《对传集》中普鲁塔克对罗马历史的记述,进而探讨其对罗马的态度。罗马建城故事广见于希腊罗马各类著作,说法繁杂不一,作者以普鲁塔克在《罗慕洛斯传》(Romulus)中对罗慕洛斯身世、勒莫斯(Remus)之死以及抢夺萨宾妇女这些基本事件的处理为例,认为著作家多采信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经过美化的故事版本,虽对罗慕洛斯有奉承之嫌,但他对传主的“偏袒”不同于希腊史家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西奥斯(Dionisius
of Halicarnasus)全然美化罗慕洛斯以示好罗马的目的,意在服务于其传记主旨,而著作中对主人公反面版本的叙述,也更说明著作家真实化传主性格以为读者效仿的初衷。(p.89-94)罗马解放希腊一事是《弗拉米尼努斯传》(Flamininus)中的核心主题,该传的取材虽主要源于波利比乌斯,但作者认为普鲁塔克在叙述中对故事多有压缩以凸显“解放者”弗拉米尼努斯的形象。“罗马权力驾临希腊是神意使然”的观点也使作者相信,普鲁塔克对于罗马统治希腊这一事实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是认同的。因此作者认为,该篇传记同《罗慕路斯传》一样,体现出著作家偏袒罗马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服务于传记目的,不应被解读为政治或外交方面的目的。(p.99)由于《对传集》中所述及的罗马传主有一半出自罗马共和末期(从格拉古兄弟[Gracchi]到安东尼[Antony]),普鲁塔克对罗马这一时段历史的观点,无疑典型体现着其对罗马的态度。作者认为,普鲁塔克对共和末期罗马道德败坏,帝制的出现大势所趋、是内战结束的必然结果等观点的认同,显然受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舆论宣传影响。然而他对庞培的褒扬和对安东尼的丑化表明,对罗马传主的褒贬均出于传记写作需要。最后作者总结道:“普鲁塔克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态度一如其于早期罗马,有偏袒,也有谴责和批评,并非循以固定模式,这些看法是其本人及其时代于此的真实反映。”(p.102)
传统观点认为,普鲁塔克撰写《对传集》有明显的政治和外交意图,即向罗马人展示希腊人先前的光辉业绩,向希腊人证明罗马人并非蛮族。但在第11章中,作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纵观整个传记集,普鲁塔克频繁强调之处在于凸显传主性格,引起读者效仿这一双重目的。主要理由在于著作家本人从未提及所谓外交或政治的意图,反而频频强调兴趣主旨在于刻画性格以为效仿典范;《对传集》中不同对传篇目之间缺乏体系化的联系,不似有其他预设的目的;传主多选择政要、将军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在于他们比诗人或艺人更能真实体现可令效仿的具体行为;对传这一形式的选择不仅在于增强传记的艺术效果,更能通过直观比较而展现不同社会背景下英雄人物可供效仿的共同美德。因此,作者认为《对传集》的写作目的在于道德教谕,而非政治外交。(p.103)普鲁塔克对罗马传主的褒贬服务于传记写作而不是对罗马文化的褒贬,《对传集》所揭示的也不是希腊罗马文化间的隔阂,反而是他们间的融合,著作家身处的世界已是“希腊-罗马”(Greco-Roman)世界,尽管希腊人和罗马人,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
第12章作者主要以《政事要则》(Praecepta
gerendae reipublicae)为例专门论述普鲁塔克的政论文,因为这些政论篇目在作者看来有独特地位,“不仅反映著作家对时局问题的看法,更有助于理解当时希腊和罗马的关系。”
(p.110)作者认为,政论主要针对与著作家身份相同的希腊社会上层,而非其所结识的罗马显贵,因而内容重在具体的行为指引而少对政体优劣的评判。就论述主题言,政论多集中于希腊城市的治理问题,具体表现在当权者不应忽视臣属于罗马帝国统治这一事实而越权行事,需谨慎对待与罗马的关系,内部应保持和谐,即使出现争端也不应诉诸外力等观点等,因此,这些政论体现出普鲁塔克的主张是“一贯而务实的”,(p.114)篇目中所使用的政治术语、所推崇的外交方式、对希腊人前往罗马求取功名的批评等都体现着普鲁塔克对时局和希腊现实问题的关注。然而作者强调,普鲁塔克的这些政论主张并不意味着他借追述希腊自由传统而反对罗马力量的介入,因为对于罗马治下希腊“有限度的自由”,普鲁塔克是默认并珍视的,他并不希望希腊人激怒罗马人而失去自治权利。从这一角度而言,作者认为“罗马和希腊上层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普鲁塔克这些政论主张的目的在于“使希腊城市的活力因符合、而非背离罗马当局的意愿而得以持续”。(p.121)
第13章是作者对整个下篇的概括,亦是对全书的总括,其核心主题在于讨论普鲁塔克对罗马的态度代表着个人还是当时整个希腊上层社会。在作者看来,普鲁塔克对罗马的赞赏是建立在批判之上的,他对罗马文化的批判并不代表敌对,而是出于和罗马人一样的担忧,是基于“希腊-罗马的”立场而非单纯希腊的立场。他对罗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希腊和罗马双重立场的合体。这种认识和态度是当时普鲁塔克所处的整个希腊社会上层共有的观点和态度,因为帝国治下所出现的希腊文化复兴,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是反罗马的,这是当时整个帝国上层(包括希腊人和罗马人)“崇古”(archaism/
antiquarianism)风尚的反映。(p.126)传统所认为的希腊史家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和琉善(Lucian)对罗马的讽刺和批评并非敌意,而是出于相对保守的思想和对道德的纯粹追求。作者认为,罗马的敌对者来自社会下层和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在财富和教育、出身阶层和权力等价连体的时代,普鲁塔克这般身居社会上层、引领时代文化风尚的希腊人是不会秉持这种态度的。帝国时期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征服表明希腊人已经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一趋势是后来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的拜占庭帝国在东部延续近千年的前奏,而普鲁塔克对罗马的态度,也是这一趋势的真实反映。(p.130)
三
纵观全书,作者对普鲁塔克生平的介绍和著作的分析虽旨在探讨其和罗马的关系,但通过著作家生平经历和思想态度间的相互作用所着意凸显的,正是希腊罗马文化融合这一时代背景。在作者看来,置身于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推崇和希腊文化复兴这一历史进程中,普鲁塔克所代表的不再是其个人,而是整个希腊社会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他的思想和态度,也是这一群体对时局的回响和时代的反映。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理路和视角,作者在书中对普鲁塔克和罗马关系的考察总体而言是客观而具说服力的。
就上篇而言,翔实的考据和精细的梳理是其主要特点。借助于“人物关系志”(prosopography)这种传记方法的使用,作者清晰勾勒出普鲁塔克生平主要节点,详尽还原和展现其中诸多细节,尤其是对于其社交圈的网络式介绍,使普鲁塔克的个人经历与其时代联系起来,于R.
H.巴罗稍前的著作《普鲁塔克及其时代》[5]以及D.
A.罗素的稍后出版的专著《普鲁塔克》相比[6],这也是其优长之处。
然而需注意的是,由于主旨在于研究普鲁塔克与罗马关系,作者上篇中多着墨于普鲁塔克与罗马的联系以及和罗马显贵的交往,这未免有夸大普鲁塔克对罗马帝国上层影响力之嫌,同时也似乎过多强调罗马帝国上层对普鲁塔克的影响。毕竟,如作者强调的,普鲁塔克和“第二代智术师”本质有所不同,(p.38)他非如普鲁萨的狄奥等前往罗马求取功名并身居要职,晚年所获得的高位多是荣誉性的。而且,作者所强调的普鲁塔克的与其他智术师的另一不同点,即普鲁塔克特殊的宗教身份——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祭司,也许正是他得以和罗马上层结识交流的机缘所在,这显然不同于第二代智术师的方式,因而作者对于德尔菲在普鲁塔克和罗马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似乎强调不够。事实上,作者既然着力叙述希腊罗马文化融合的背景,那么作为希腊文化的圣地,德尔菲无疑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罗马皇帝对德尔菲的重视和青睐,如尼禄在皮西亚赛会(Pythian
Games)上宣布希腊自治,图拉真和哈德良对德尔菲圣所的增建,都说明这一身份可能才是普鲁塔克结识罗马上层的真正平台和契机。因此,过于强调普鲁塔克对于“第二代智术师浪潮”中的先锋作用未免言过其实,而且这也可他对于自己前往罗马政务细节的缄默,以及从未提及自己罗马公民身份的事实得到说明,作者对此缄默态度的解释显然是牵强的,即使普鲁塔克不是如作者所言的“政治上微不足道”,(p.21)他至少对此并不认同。
下篇作者对普鲁塔克几类作品的分析是概述式的,这显然由于作者意在对普鲁塔克“罗马观”的概观,而非对普鲁塔克作品面面俱到的详述。总体而言,作者虽然对著作主题的概述式分析难免失于简略,但对著作特点的把握和普鲁塔克观念倾向的推理分析都客观而合理,尤其是对于《对传集》普鲁塔克写作目的“道德论”的分析,几乎成为后来普鲁塔克这一主题研究的范本。当然关于对传(parallel)这种传记形式的采用和写作目的间的联系学者仍存争议,如学者达夫的“文化反抗说”[7]和塔图姆的“文化竞争说”,[8]这里暂不赘述。
笔者以为下篇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普鲁塔克拉丁语水平的误解。作者以普鲁塔克在《德摩斯梯尼传》序言中自述造访罗马期间因公务繁忙无暇练习拉丁语,直到晚年才集中研习拉丁著作的事实为基础,推论得出普鲁塔克的拉丁语水平不足以阅读使用拉丁史料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原文中普鲁塔克此段自述的意图在于为下文的写作角度做铺垫,即自己因闲暇时间和精力所限无法进行拉丁语系统训练以欣赏拉丁语文体的简洁有力,以及演说词的变化和韵律之美,言外之意即尚不足以欣赏和完全理解演说家西塞罗的作品,因此将自己传记的重心侧重于叙述两位传主的行动和政治生涯为主。[9]显然,不足以欣赏体会西塞罗演说词之美并不意味着著作家不具备阅读一般史著的水平,因为演说词之难,是古今学者的通识。这样,作者对普鲁塔克在《帝王传集》和《对传集》中拉丁史料使用方式的批判便有失公允,(p.77;p.82-84)尽管作者所推测的其他几种方式也不无可能,但普鲁塔克对拉丁史料的亲自阅读是可能的,而且这并不和其他几种方式相矛盾。
总体而言,C. P.
琼斯的这本《普鲁塔克和罗马》无愧于普鲁塔克研究的经典之誉。作者所秉持的研究视角,即从时代背景出发考察著作家的思想渊源和著述风格俨然成为著作家个案研究的基本范式,而作者其中对原始文献的注重与娴熟引用,也是国内世界史研究者当下最须学习的治史态度与方法。另外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端,即为凸显新观点而对原典所作的一些断章取义的解读,也需读者和研究者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