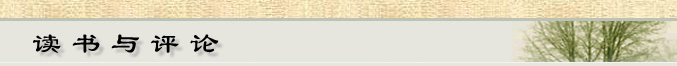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
对国内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普及读物的批评和改正[1]
刘昌玉,吴宇虹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提
要]
近几年来,国内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普及读物出版近十本,然而粗制滥造的文风使一些普及读物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甚至是十分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为了让广大国内业余读者不被这些“商业书籍”中的错误所误导,也为了我国世界史研究学术风气的健康发展,本文就这些书中的错误之处进行批评与改正。
[关键词]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普及读物;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亚述学
近十年国内出版的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普及读物是:李铁匠《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陈毛书”);赵树贤《巴比伦:沉睡文明的梦与醒》,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赵书”);郑殿华、李保华《走进巴比伦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第2版(以下简称“郑李书”)及刘卿子《两河流域:逝去的辉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刘书”)张健、袁园《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张袁书”)。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旧译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全境、叙利亚东部、土耳其南部和伊朗西部地区。时间段是从大约公元前四千纪的乌鲁克文化期直到公元前331年波斯帝国的灭亡。这些普及读物书名多为“巴比伦文明”,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巴比伦”文明只能定义两河流域南方从公元前1800至前500年的古巴比伦、中巴比伦和新巴比伦三个文明分支时期,不能代表包括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及北方地区亚述在内的整个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和文明。
上述读物除李铁匠和郑李书的错误很少外,其余几本存在有大量错误,很多是常识性错误(“硬伤”),尤其是对于书中所引用的图片的解释更是可以看出作者的业余水平和草率之极的工作态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楔形文字文献的学科是亚述学。我国的亚述学已经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逐渐开展起来,并有了可以释读楔形文字的亚述学者,使我国亚述学研究在国际亚述学界具有了一定的影响。[2]我们作为专门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亚述学者,有责任对这些错误进行指正和批评,以免这些错误误导广大的读者,特写此文,提出商榷。
一、几本书中存在的传袭错误
几本书的作者对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生疏,而且还不亲自查找外文书籍和国内专家撰写的有关著作,而是借助现成的几本有错误的中文书籍抄来抄去,以致“以讹传讹”、“错上加错”,误导了渴求知识的广大读者。
1、“萨尔贡一世”称呼错误,人物混淆。
郑李书第163页,刘书第23、27页,陈毛书第34、35页,张袁书第46、64、65、242页中都把阿卡德帝国的建立者称为“萨尔贡一世”,这种称呼是错误的,正确的称呼是“阿卡德的萨尔贡”(Sargon
of Akkad,公元前2291-前2236年)或简称“萨尔贡”(Sargon)。在国外非专业书中也偶尔称为“萨尔贡大帝”(Sargon
the Great)。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历史上,共有三位称为“萨尔贡”的国王,分别是阿卡德帝国的建立者萨尔贡和亚述王朝的两位萨尔贡:古亚述城邦的国王萨尔贡第一[3](Sargon
Ⅰ,大约公元前1920–前1881年)和新亚述时期的国王萨尔贡第二(Sargon
Ⅱ,公元前721-前705年),所以真正称为“萨尔贡一世”的人正是三位同名国王中最不著名的古亚述国王。其实早在1998年所出版的《世界历史名人谱:古代卷》一书中的“萨尔贡二世”一条中,其编者刘家和先生就指出:“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上,先后有过三个名叫萨尔贡的国王。第一个是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王萨尔贡,……第二个是公元前19世纪的亚述王萨尔贡一世,关于他的事迹,现在几乎一无所知(本文作者按:萨尔贡第一有王铭和印章出土[4])。第三个就是……亚述王萨尔贡二世。”[5]
所以如果这几本书的作者稍微用心查一下专业中文书,研究一下几个萨尔贡的区别,不急于求成抄别人的错误,也不会出现继续犯错的结果。
2、亚述国王名的严重错译:“巴尼拔”、“亚述王鲁巴力特”、“纳西尔帕二世”
赵书22页“亚述王巴尼拔”,46页“巴尼拔”,张袁书19页“亚述国王巴尼拔”,
81、169、175页“巴尼拔”。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强大的国王是楔文拉丁化dAššur-bāni-apli(公元前668-前627年),英文是Ashurbanipal,专业中文书译为“阿淑尔巴尼帕”(文革前有译为“亚述巴尼拔”也不妥,因为亚述为地名Assyria的音译,阿淑尔才是神名和城Aššur的音译)。这些王名错误的共同点是把人名中的神名或城名“阿淑尔”当作王的头衔。同类错误有:赵书28页“亚述王鲁巴力特”和张袁书75页“亚述王鲁巴力特”的英文Aššur-uballit应译为阿淑尔乌巴里特;赵书30页“纳西尔帕二世”,张袁书18页“亚述国王纳西尔帕”和76页“亚述国王纳西尔帕二世”的英文Ashurnasirpal
Ⅱ应译为阿淑尔那西尔帕第二。
3、“恩利尔是风神”的错误
郑李书118页;刘书63页(甚至23、41页还称恩利尔Enlil为天神,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天神是安An);陈毛书99页;张袁书94页都一致地把恩利尔(即我们系统化音译的“恩里勒”)解释为“风神”,这是错误的,恩里勒是“空间之神”、“天地之间(人界)之神”,而两河流域的风神是阿达德(Adad)。这一错误应该是来自对外文书中dEn-líl的词源“空间之主”的误解,遗憾的是,这一共同错误在这几本读物多处出现,千篇一律,甚至一字不差。
二、对赵树贤《巴比伦:沉睡文明的梦与醒》一书错误的改正
1、第12页上图的图片介绍为“阿卡德与基什国王萨尔贡的黄金面具”,其错误之处是“黄金”二字,这一著名的头像或面具在许多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书籍中都曾引用过,可是说它是由黄金制成的却只有这本书。它的真正材料应该是青铜(Bronze)
。[6]
同一页的下图的介绍是“(阿卡德的)萨尔贡宫殿的双翅牛神”,这明显是亚述帝国时期萨尔贡二世宫殿的浮雕像,而书中相应的文字却在叙述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图片与文字所介绍的年代相差大约1700多年。
2、第15页“这一切,阿卡德的孙子纳拉姆辛在梦里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句话的错误是“阿卡德的孙子纳拉姆辛”。正确的表述应该为“萨尔贡的孙子纳腊姆辛(Naram-Sin,公元前2211-前2175年)”或“阿卡德王萨尔贡的孙子纳腊姆辛”,我们知道而萨尔贡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瑞穆什(Rimush),瑞穆什的继承者是他的兄弟马尼什图苏(Manishtusu),马尼什图苏的继承者是那腊姆辛,所以他是萨尔贡的孙子。“阿卡德”是一个地名,这一典型的常识性错误反映了作者基础知识的可怜。
3、第19页下图介绍为“古巴比伦的黄金短剑”,这明明是著名的乌尔王墓出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的黄金短剑。而作者在“古巴比伦-汉谟拉比”这一节中插入了早王朝时期(乌尔第一王朝)的图片,反映了作者时间概念的混乱。古巴比伦时期是公元前1800-前1500年,乌尔王墓时间为公元前2600年,这前后相差1100年的历史。作者多插入图片增强本书的观赏度的初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图片的说明犯有严重错误,误导读者很难原谅。
4、第28页下图“亚述国君坐像”,也是严重错误。这尊无头坐像是从苏萨(Susa,今天的伊朗境内)出土,大约的时间是乌尔第三王朝至伊辛王朝时期(公元前2100-前1800年),[7]不知作者根据什么说它出土于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并认为他是一位亚述王。作者对自己不了解的文物任意指认是非常不严肃的学术风气。
5、第71页的小标题为“(波斯王)青年居鲁士”,作者令人吃惊地插入第72页上图“驾着战马围猎雄狮的国王雕像”的图片,这里图和文的错误有好几处。首先是书中这一部分叙述的是波斯帝国国王居鲁士,插入的却是新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帕的壁浮雕,二者不在同地,相差百年以上,而且此图中并无猎狮,根据国外研究,本图是出土于尼尼微的新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帕北宫的雪花石膏浮雕,描绘了国王阿淑尔巴尼帕骑在马上猎杀野生驴的场面。[8]最后是一个常识性错误“雕像”,而原图片却是浮雕。雕像与浮雕是不同的文物。
本节第72页下图描述“一位波斯男子怀抱山羊祭品的金铸雕像”,其错误还是时代错误。因为此图是苏萨出土的中埃兰时期(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雕像,[9]那时的居民为埃兰人,而非波斯人。把此图放在介绍“居鲁士”一部分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可见作者“指鹿为马”的写作胆量。
6、第86页描述为“亚述军队的所向披靡使巴尼拔可以搜集到大量的泥版图书”,其第一个错误是“巴尼拔”,而应该是阿淑尔巴尼帕,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文解释过。第二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移花接木”,因为此图并非什么“亚述军队”,而是与之相差近2000年的早王朝时期的苏美尔的拉旮什(Lagash)城邦公侯埃安那吞(Eannatum)的军队。图中的这块浮雕就是十分著名的“埃安那吞鹫碑”的一部分,描绘了拉旮什公侯埃安那吞与温马(Umma)军队作战的场面。此图片在许多书中都被引用,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历史十分出名。
7、第91页上图的“迦勒底人像”(公元前626-前539年),其描述也是错误的。此雕像是典型的苏美尔人像,其年代应该是在早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2900-前2685年)。[10]前后相差2000多年。
三、对刘卿子《两河流域:逝去的辉煌》一书错误的改正
1、第17页下图所示“古代的苏美尔雕刻艺术”,其错误之处是将十分出名的新亚述王阿舒尔巴尼拔王宫出土的大型浮雕当成了苏美尔人的艺术。我们知道,在阿舒尔巴尼拔王宫出土了大量的浮雕艺术,有战争、狩猎等题材。而此图片所描绘的是国王阿舒尔巴尼拔正其在马上手持长矛刺杀猎物的场面。[11]
2、第22页“城邦的王被称为卢伽尔、拍达西、恩或恩西”一句。在苏美尔语中,“王”称为Lugal,音译为卢旮勒,词源学分析是:lú是“男人”之义,gal是“伟大的”之义,合起来就是“伟大的男人”,用来指国王;而所谓的“拍达西”是恩西(énsi,“公侯、总督”)的会意楔文符号的字形分析,早期的研究不知这一会意符号的读音,暂写作(同大写字母)PA.TE.SI,后来学者们发现这三个符号的读音énsi,无人再读为PA.TE.SI了。“拍达西”、“恩西”是同一个头衔,地位比国王低,早期有独立性,写作énsi
(PA.TE.SI)。恩(en)有两个意思:一是“主人”,二是神庙最高祭祀,并不专指城邦的王(史诗中远古王用这一称呼),不是王的专门称呼。
3、第23、41页“天神恩利尔”的正确表述为“众神之王恩里勒”,天神是安(An),阿卡德语为安努(Anu);40页“日神安”的正确表述为日神乌图(Utu),阿卡德语为沙马什(Shamash);65页“阿舒尔神,亚述人的太阳神”的正确表述为阿淑尔神是阿淑尔城的主神,在新亚述时期为最高神,从来不是太阳神,两河流域的太阳神是沙马什。
4、第100页图片描述“伦敦大英博物馆内一个公元前2600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的音乐盒”。这幅图片是十分著名的乌尔军标(Standard
of Ur),出土于乌尔王陵,是苏美尔镶嵌艺术的精品,正反两面分别是“战争”与“和平”图案。真不知作者如何能够将之与音乐盒联系起来。
四、对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一书错误的改正
1、第33页图片的描述“苏美尔人塑造的神的形象,与我们今天塑造的外星人的形象极为相似。”其错误之处在于“神的形象”一语,我们知道,在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中,神的形象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头上带角,这是神的标志。而图片描绘的是一群“崇拜者”、“祈祷者”的形象。它们出土于埃什嫩那(今阿斯马尔Asmar土丘),都是早王朝时期的作品。这些雕像藏于伊拉克国立博物馆和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12]另外,不知作者如何知道外星人的形象的。
2、第51页“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也自称是‘众神之王’,宣扬王权神授。”首先这是一个病句,“众神之王”与“王权神授”岂不是自相矛盾?都是众神之王了,还用神来授权为王吗?这是纯粹语言逻辑错误。更严重的是概念错误,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整个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王敢自称“众神之王”,早期仅有少数王自称为神。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最先称神的国王是阿卡德王那腊姆辛和他的继承者沙尔卡里沙瑞(Shar-kali-sharri,公元前2174-前2150年),接下来称神的是就是乌尔第三王朝的第二个王舒勒吉(Shulgi),他的三个继承者和随后的伊辛、拉尔萨王朝诸王。当阿摩利人的巴比伦王朝统一天下时(即汉穆腊比时期),他们放弃了称神的做法,从此,在两河流域王权一直低于神权。[13]
3、第54页图片解释“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此句话的错误在于“最古老的”,我们知道,现存最早的法典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乌尔那穆法典》,而古巴比伦时期的《汉穆腊比法典》则是两河流域文明保存最完整和条文最多的法典。
4、第79页图表“楔形文字的演变”,表中的“山”的楔形符号错译为“果园”,“果园”的楔形符号错译为“山”。
5、第98页“对太阳的崇拜,无疑是苏美尔人最古的信仰,他们称太阳神为‘沙玛什’,即光明之神。太阳每天晚上从遥远的北方赶来,乘坐一辆火轮车,把光明赐给人间。”首先,太阳神是苏美尔人最古信仰的诸神之一,文献未见“太阳每天晚上从遥远的北方赶来,乘坐一辆火轮车……”的表述,而是太阳从东方的地下升起,乘坐战车;其次,说“他们(苏美尔人)称太阳神为‘沙玛什’”混淆了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稍微有点楔形文字基础的人都知道,在苏美尔语中,太阳神是乌图(Utu),而沙马什(Shamash)是阿卡德语称谓的太阳神。
五、对张健、袁园《巴比伦文明》一书错误的改正
这本书可能是目前最新的关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介绍的普及读物,于2008年9月出版,是所谓的“家庭书架·文明读库”系列20本中的一本。全书共284页,号称28.4万字,书中前言部分说:“此书的着重点是:在已有的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认识的基础上,尽可能全面介绍该文明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让读者在这本通俗读物的引领下,能对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有更透彻的认识……”作者的确写得内容不少,但是抄袭的错误和自己独创的错误很多,甚至荒谬。下文将就这本书的错误逐条批评和改正。
1、第41页上图标题为“苏美尔人制造的金勺”,介绍为“可能是用来盛放啤酒或葡萄酒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勺,而是一个过滤勺、漏勺(strainer),从大英博物馆的官方网站(www.britishmuseum.org)可以找到这一金制的艺术品。[14]它出土于乌尔王墓的女王墓中,它的作用也不是“盛放啤酒或葡萄酒”,而是用来过滤啤酒或葡萄酒的渣滓。
2、第42页图片解释“第三王朝(公元前2500-前2400年)时期”,第63页下图解释“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550-前2500)”(实际是古苏美尔时期拉旮什城邦即拉旮什第一王朝文物),第134页下图解释“第二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00年)”,第273页上图解释“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550年)”(这也是古苏美尔拉旮什第一王朝时期文物)。这些“第二王朝”、“第三王朝”到底指的是哪一个第二、第三王朝?我们知道,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有著名的“乌尔第三王朝”和“伊辛第二王朝”(中巴比伦时期)以及早王朝时期的“基什第二王朝”、“基什第三王朝”、“乌鲁克第二王朝”、“乌鲁克第三王朝”、“乌尔第二王朝”和“拉旮什第二王朝”(即古地亚王朝)。称第二王朝、第三王朝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3、第45页上图“苏美尔人制作的陶塑女子像”(大约公元前2900-前2000年),这一个塑像并非苏美尔人的作品,而是哈拉夫文化时期(公元前6000-前5300年)的史前原始社会母神像。[15]
4、第49页图片的标题为“亚述士兵押解战俘浮雕”,解释为“……表明4000多年前的雕刻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平。”这又是一处自相矛盾的错误。这幅图片是新亚述时期的作品,[16]
时间大约是公元前900-前600年。而这本书中所说的“4000多年前”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表明作者对亚述历史分期和各时期的文物的了解十分可怜。
5、第65页图片的解释的最后一句话“……定都阿卡德(即后来的巴比伦城)”,这完全是个笑话。阿卡德和巴比伦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至今亚述学和近东考古界还不知道阿卡德在哪里,只能根据文献和文物大致推测其可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支流迪亚拉河地区(有文物发现)。而巴比伦城遗址位于今天伊拉克Babil省的Al
Hillah地区。作者说“阿卡德即后来的巴比伦城”这种天大的谬论反映了作者对两河流域文明的无知程度。
6、第66页上图的标题是“阿卡德王朝萨尔贡皇帝二世宫殿门口的翼牛人首兽”。而图片却是著名的新亚述国王萨尔贡第二宫殿的雕像作品。作者是将阿卡德王萨尔贡(公元前2291-前2236年)与亚述帝国时期国王萨尔贡第二(公元前721-前705年)相混淆了。
同样,本页下图的标题“带翅膀的阿卡德国王”,其下解释却是“此雕像制作于公元前8世纪末的萨尔贡二世宫殿”,作者居然不知古阿卡德和亚述是两个不同的时期。
7、第67页“纳拉姆辛是阿卡德的孙子,在梦里,他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一句与赵树贤《巴比伦:沉睡文明的梦与醒》一书的第15页“这一切,阿卡德的孙子纳拉姆辛在梦里都看得一清二楚”一句竟然如此相似,作者仅仅将赵书中的有错语的叙述顺序一换就全盘引用了。这种错误与其说是作者专业知识的无知,不如说他在抄借别人的拼盘时,把别人盘子里的苍蝇也搬过来了。其错误已在前文指出。
8、第69页的图片标题为“汉谟拉比青铜雕像”,而下面的解释是“一尊黑色花岗岩雕凿的帝王头像,与汉谟拉比法碑上的帝王形象十分相似……于是这个头像被认定为汉谟拉比的肖像”。标题说是“青铜雕像”,在解释中又变成了“花岗岩雕凿的帝王头像”,这么明显的语病,恐怕非专业的读者也会轻而易举的指出。更重要的是,作者所说的“青铜”和“花岗岩”质料全都说错了。这一个头像的真正质料应该是闪长岩(Diorite)。[17]
9、第82页叙述新巴比伦帝国时多处提到“尼布甲尼撒”这一名称,是容易引起混淆的。因为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共有两位叫做“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国王:第一位是伊辛第二王朝时期(the
Second Isin Dynasty)最伟大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第一(Nebuchadnezzar
I,大约公元前1125-前1103
年),他最著名的事迹是重建了被埃兰人所摧毁的巴比伦城;第二位就是更为著名的新巴比伦王国(又称“迦勒底巴比伦王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第二(Nebuchadnezzar
Ⅱ,大约公元前630-前562年)。最好不要简单的把新巴比伦国王称为“尼布甲尼撒”,而应先称为尼布甲尼撒第二,然后再使用其容易混淆的原名。
10、第90页图片的标题为“苏美尔女神像”,此处错误更是荒唐无知。这张图片应该是库提人统治时期的拉旮什城的公侯古地亚(Gudea,大约公元前2144-前2124年,男人!)的十分有名的雕像。
11、第115、135页图片标题为“亚述书吏像”,此雕像并非什么亚述书吏,而是出土于马瑞的早王朝时期典型的苏美尔人雕像。[18]
12、第116页“苏美尔人发明了苏美尔语,阿卡德人发明了阿卡德语”一句,将语言与文字的概念混淆,苏美尔人发明的是苏美尔楔形文字,而阿卡德人则是借用了苏美尔人所发明的楔形文字符号用于阿卡德语,语言不是什么人发明的,而是在人类社会自然产生的。
13、第124页“在乌鲁克、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许多古代遗址”一句将古今地名混淆。乌鲁克(Uruk)是古代城名,遗址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而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则是现在的国家名,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并列叙述?把乌鲁克城放在伊拉克之外,伊拉克政府一定会提出抗议的,这一错误可能造成外交麻烦。
14、第126页“美国有一个名叫史氏的女学者”,试问:“名叫史氏”作何理解?引文应严肃使用外国人名的全姓译文施曼特-贝塞腊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她花了近20年时间写了一本名叫《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的书,详细阐述了陶筹文字起源学说,并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关于此人,我国学者何丹也在其书中详细论述过。[19]
15、第129页图片的标题是“波斯波利斯宫殿遗址”,下方解释为“约建于公元前521年,现位于伊拉克。”作者说“波斯波利斯位于伊拉克”,这可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知道,波斯波利斯遗址位于伊朗境内。试想:如果此书被伊朗人或伊朗学者看到,他们又会如何看待中国的学术界,有甚者可能引起外交争议,中国人出版的书中说伊朗的遗址位于伊拉克了,伊朗方能够坐视不管吗?说严重点,这是侵犯人家的领土主权!
16、第150页图片的标题是“《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局部”,下方解释为“该法典碑是法国考古学家在今叙利亚境内发掘的。”与上一条一样的错误。我们知道,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是1901年由法国人Gustave
Jéquier在今天伊朗境内的苏萨遗址(今Khuzestan地区)发掘的。它是在公元前12世纪由当时的埃兰国王Shutruk-Nahhunte从巴比伦城带回首都苏撒作为战利品。今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作者又将伊朗境内发现的文物说成了叙利亚,真不知此处和上处涉及领土问题的错误被伊朗人看到之后会做何感想?这不仅是对伊朗文明史的挑衅,也误导国内广大读者,为了避免书中出现涉及外交问题,我们呼吁国内出版界在批准此类“垃圾书籍”出版时要千万谨慎才是。
17、第134页下图解释“发现于吉尔苏古城特洛赫”错误。吉尔苏(Girsu)为古代名字,今天称此地区为泰罗(Tello),应改为“吉尔苏城遗址泰罗”。
18、第135页“楔形文字的符号总共不到600个”。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楔形文字常用符号600个左右,所有文献中出现的苏美尔语楔形符号总数超过1500个(包括许多不常用符号)。[20]
19、第148页“《汉谟拉比法典》……把社会分成3个等级……第二阶层是国家的保卫者”,关于《汉穆腊比法典》,国内许多历史教科书中多有介绍,第二阶层称为“穆什基努”(muškēnum),意思是半自由民,不是“国家的保卫者”。
在第149页关于《汉穆腊比法典》,作者叙述“一名妇女如果忽视了家务并羞辱了她的丈夫,那么她将被迫接受‘水审’,也就是将她扔到最近的河流中,由河流来裁决……”此处的错误是作者对于《汉穆腊比法典》不懂和乱抄,而且还抄错了。作者将法典的第132条的后果与143条的前提“张冠李戴”了,143条是:羞辱丈夫的妇女应该被投入河(淹死),而不是河神审判;132条是用河神审判。[21]
20、第158页下图的标题为“苏美尔圆筒印章”,而其解释则是“这个圆筒印章描绘了动物打斗的场面,青铜时代后期制作(约公元前14世纪左右),来自塞浦路斯,……”试问作者:苏美尔圆筒印章怎么能晚到约公元前14世纪左右制作?我们知道苏美尔的历史从大约公元前3200年至前2000年。而在前14世纪已经是中巴比伦王朝和中亚述时期了。
21、第160页“在‘迪提拉’文件中还提到一种被称为马什吉姆的人,他们可能是一种法庭书记员”一句讲到了“迪提拉”(di-ti-la),意为“最终裁决”,而马什吉姆(maškim)指的是“王室代表”(“钦差”),并不是什么法庭书记员,这些王室代表不仅出现在法庭中作为案件监督,还在各种祭祀、外交等事务中作为有关王家事务的执行人。作者不知道古代两河流域名词的基本意思,只能音译,自己不明白,读者也读不明白。
22、第163、175页图片标题为“亚述国王巴尼拔雕像”,首先的错误是人名、地名不清楚,应该是“阿淑尔巴尼帕”(Ashurbanipal)。更为严重的错误是:这幅图片描绘的并非是阿淑尔巴尼帕,而是另一位亚述国王阿淑尔那西尔帕第二(Ashur-nasir-pal
Ⅱ)。[22]
23、在“学生自叙学校生活”的标题下,第171页图片的标题“老师和学生们(雕像)”,作者大胆地把埃什嫩那神庙中的崇拜者、祈祷者的雕像胡乱说成是老师和学生。此雕像在前文中(四,1)已经介绍指正过。
24、第173页图片标题“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灰石片”,下方解释为“英国牛津鸦片战争博物馆收藏”,真是一语惊人!发动侵华鸦片战争的英国何时有的“鸦片战争博物馆”!真是可笑到了极点。其实这幅图中的石灰石片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阿什摩利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全名为Ashmolean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博物馆),[23]
作者不会无知地把Ashmolean翻译成“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吧。这一可笑又可愤的低级错误真是对不起广大读者。
25、第188页“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中,农村和城市都称为uru”一句,是对楔形文字不懂而造成的低级错误。因为稍微有点楔形文字基础的人都会知道,uru一词是苏美尔语,意为“城镇”,而阿卡德语“城镇”一词是ālu。作者完全不知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其余一些错误如下:第40页图片标题“抱着小狮子的雪花石膏人像”中的“人像”应改为“英雄形象”,可能是吉尔旮美什;第47页的“另一支闪米特游牧民族库提人消灭了萨尔贡帝国”,“库提人”并非塞姆(闪米特)民族,对于其民族至今不清楚;第131页“22岁的德国学者朱利斯·欧佩尔特在这一点上最值得一提的,……”中对于欧佩尔特(J.
Oppert)的国籍问题我国亚述学者拱玉书教授在其《西亚考古史》一书中注释到:“奥佩尔生于德国汉堡,父母都是犹太人。曾在海德堡、波恩和柏林学习。后来到法国,先以教德语为职,后成为法国著名亚述学家和考古学家,任职于法兰西学院。”[24]
欧佩尔特出生于德国,他的学术生涯是在加入法国国籍以后,所以说他是法国学者;第165页图片标题“泥版印章”的表述错误,“泥版”应写为“泥板”,它与印章是两种不同的物品,不能用来修饰印章,而原图所描绘的应该是圆筒印章;第195页上图解释为“祭祀苏美尔风暴之神恩利尔……”一句的恩里勒(恩利尔)应该是“众神之王”,而风暴之神为阿达德,前文已述。
在我们写作这一批评文章时,作为中国学人,我们常常因国内出版的这些书中的严重和过多的错误而感到羞愧,甚至气愤。为了避免今后出版物出现类似现象和明确错误的责任,我们建议所有的普及读物应该注明所用的中英文参考书籍,一是提高读物的编写标准,二是如果引用了别人的错误,也可避免自己担责任。为了避免外文专有名词中译法各自为政造成的一名多译的混乱现象,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正在实行译名系统化和标准化的做法,也希望出版界同事和作者们能够支持和使用我们的译名系统。如果本文严厉的批评使有些作者感到了难堪,这并不是我们批评的目的。我们焦虑的是,如果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不展开学术批评和讨论,错误百出、低水平重复性和误导读者的出版物就会越出越多,不认真写书而是快速编书抄书的学风将愈演愈烈,这将严重损害中国在世界文明和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国际声誉,打击了那些以科学态度严肃认真从事科研和普及工作的作者们的积极性,会对中国的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1]
本文的外文专有名词的汉字音译根据“古典所中西文专有名词音对译字表”,载吴宇虹等:《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楔形文字经典举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2]
有关亚述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请参考:吴宇虹《亚述学在中国》,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第101-109页。
[3]
本文作者认为“一世”、“二世”等称呼不妥,因为这些国王许多只是同名关系,之间并无父子继承关系,所以应该称为“第一”、“第二”等。
[4] 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to
1115BC),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Volume 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p.45-46
[5]
朱庭光主编;施治生、郭方分卷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古代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第46页。
[6]
参见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ⅩⅩⅢ
[7]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150
[8]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258
[9]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184
[10]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91
[11]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254
[12] Dominique Collon,
Ancient Near Eastern Art, British Museum Press,1995. p.61
[13]
刘文鹏、吴宇虹、李铁匠,《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14] http://www.britishmuseum.org/explore/highlights/highlight_objects/me/g/gold_strainer_for_beer_or_wine.aspx
[15]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6
[16] Pierre Amiet,
L’art Antique du Proche-orient, Mazenod Paris 1977, p.416
[17]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149
[18]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89
[19]
参考:D.S.
Besserat, Before Writing,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以及何丹《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关于人类文字起源模式重构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
参考:R.
Borger, Mesopotamisches Zeichenlexikon, Münster
(2003)与A.
Deimel, Liste der archaischen Keilschriftzeichen (WVDOG
40; Berlin 1922)二书。
[21]
吴宇虹等,《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132条:如果一个人的妻因为另一个男人的缘故,(舆论)指责都指向她,然而,她并未被抓住与另一个男人睡觉,为了她的丈夫(的名誉),她应该经受河神审判(跳入神河)。第114页143条:如果她(一个妇女厌恶丈夫)不守身而是出门(玩乐),浪费她的家财,羞辱她的丈夫,人们应该将那个妇女投入水中(处死)。
[22] Eva Strommenger,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图197
[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Kish_tablet
[24]
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