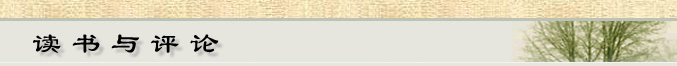读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杨孝本
[提
要] 欧文·拉铁摩尔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其研究范围涉及边疆史、民族史和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尤以边疆史领域成果卓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即是其以边疆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作。本文在梳理欧文·拉铁摩尔学术生涯的基础上简要介绍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成书过程,并对其结构和内容作了大致勾勒,然后就著作的特点和学术价值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欧文·拉铁摩尔; 过渡地带; 亚洲内陆;边疆;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1]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第一位外国院士。因其幼年曾居中国,后常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正是基于其复杂的生活经历和多元的文化视角,拉铁摩尔在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打破了以汉地社会为本位的边疆史研究传统,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见解。本文拟在考察拉铁摩尔社会生活和学术背景基础上,介绍该书的内容要点,并就其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独特视角谈一些自己的心得。
[一]
欧文·拉铁摩尔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成书
在解读和阐释其著述之前,有必要对拉铁摩尔的学术背景作必要的考察,只有切实把握其人生轨迹,置其作品于特定的背景,方能较为公正准确地评价他的成就。
1﹒其人[2]
欧文·拉铁摩尔,1900年7月29日出生于美国。其父大卫·拉铁摩尔是一位精通法、德、希腊和拉丁文的语言教师,曾到中国上海,后又辗转天津任教,欧文·拉铁摩尔也在天津度过童年。12岁那年,因父亲不想让自己的子女“讲着中国话长大”,送他到瑞士读书,两年后,又进入英国坎伯伦的圣比斯学校,其后,他争取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失败,沮丧中返回中国天津与父亲会合,并开始任职英国Arnhold进出口贸易公司,时年19岁。这份工作需要外出较多,而使他得以广泛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有机会与各阶层的人士接触,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商人、地主、土匪、农民,他为军阀张作霖作过翻译,也与普通的中国员工一起吃过饭。如其后来回忆,旅行赋予了他远远超过攻读博士学位所获得的识见。
1925年赴蒙古地区的一次贸易旅行,被拉铁摩尔视为自己人生的转折。当时他被派赴归化(今呼和浩特旧城),负责交涉一列装载羊毛的火车的通行问题,他见到了令他从此着迷的骆驼商队,“骆驼队与铁路货车之间堆放着货物。彼此间只是两步到四步的距离,却联系起了了两千年的历史。千年间,商队缓慢往来于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未知旅途。而时代的潮流,正在毁灭过去,开启未来”。[3]而后,他辞去工作,追随商队穿越中国西部内陆到达印度,探寻古老商路。这也是拉铁摩尔研究亚洲内陆地区的开端。
连接东西方的亚洲内陆广袤地区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千百年间,商旅、冒险家、军事家、朝圣者往来其间,或追求奢华财富,或觅求骄人战功,或向往虔诚信仰。拉铁摩尔沿途考察古今商路异同。随后出版了《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和《鞑靼高地》两本著作,记述了这段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1929年至1930年,拉铁摩尔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旅行,后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满洲的蒙古人:其部落划分、地理分布,与满人和汉人的历史关系以及当前的政治问题》。1938年,拉铁摩尔应邀至美国霍普金斯学院的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任职。两年后,《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出版,这本耗时多年的著作,是其集研究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大成之作。以后的二战及战后的一段时间,他的研究中心向国际形势转移,相继有《美国与亚洲:今日战争问题与未来和平》、《亚洲的决策》、《亚洲的局势》等著作问世。从1928年的商路之旅到战前,一系列相关著作的发表奠定了他在亚洲内陆和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地位。
2﹒其书
如前所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成书于1940年,但“这一本书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4],从拉铁摩尔早年游历中国东北开始酝酿构思,至任《太平洋评论》杂志编辑期间开始写作,再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间完稿,前后沿延十余年。是书融旅行见闻和学术分析于一炉,既有穿梭于不同族属的所见所闻的生动描述,又有对不同国家、地区社会历史、语言风俗的细致考证和精辟分析。
作为拉铁摩尔边疆史地研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共四部分,第一部分“长城的历史地理”具有总论性质,从陆权和海权的讨论入手,重新确立了亚洲内陆边疆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然后沿秦长城一线讨论了边疆过渡地带:黄土地区,蒙古高原,满洲的农田。森林和草原,中亚的绿洲和沙漠以及青藏高原等地区的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以及历史的演进。卷二至卷四又用9章,分“传说时代和早期历史时代”、“列国时代”、“帝国时代”三个阶段,梳理了长城以南的农耕社会和以北游牧社会确立过程,并恢复了游牧民族在中国边疆矛盾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农牧文明的互动中阐释了中国的边疆历史。在书中,拉铁摩尔将中国的边疆社会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细致的考察,就中国文化的起源与扩散、游牧民的定义和游牧社会的兴起、“贮存地”理论、长城的评价、草原的边缘地带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并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有独到之处,文章以下内容仅就几点谈一些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理解。
其一、游牧民与游牧社会的兴起
古人在对比农耕、游牧两种文明时描述到:“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5]但史籍中未有这种差异出现——亦即游牧民族形成时间的明确记载。《史记·匈奴列传》是最早系统描述这个独立于汉地社会之外的游牧社会的史料,但是,司马迁追溯游牧民历史至上古时代的说法也给人们带来错觉,致使部分国内学者往往将先秦史籍中出现的禹之西戎,殷之鬼方,周之昆夷,猃狁等戎狄蛮夷,都视为草原游牧民,并且用后世游牧民入侵中原的阐释模式来解读当时的华夏——蛮夷关系,认为中原王朝很早就处于对抗草原游牧民的历史循环中。[6]拉铁摩尔根据自己的考察否定了这一传统的看法,他认为蒙古草原游牧民的产生是在公元前3、4世纪,并认为中国应该是先有农耕文明,而后有游牧文明,这个观点也否定了时人囿于单线程的“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进化论影响,认为农业作为相对高级的文明,是从定居的畜牧业中产生的观点。相反,拉铁摩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汉人的进化促生了后来与其对峙的游牧民族。
在他系统梳理的早期文明历程中,新石器时代散居于中国各地的原始民生活方式大致相同,基本是对原始行为的因袭,采集、挖掘、猎杀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营集原始农业、畜牧、采集和渔猎为一体的混合经济,只是由于各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同而在组合上彼此有所差异。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心的黄土地带,由于其土壤易于耕作,农业率先专门化生产,农业对灌溉技术的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组织的进步。社会的进化带来的是有选择的地理扩张,人们利用自己相对先进的技术条件,在寻求更广阔的可耕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华夏——蛮夷”的区别。华夏即建立精耕灌溉农业地区,而“蛮夷”则无疑是对抗这种进化主流的族属。早期史书,时有“蛮夷戎狄”的记载,往往有史学者视其为游牧民族。拉铁摩尔认为,这时的汉地社会尚未拓展到北部草原的边缘,这些蛮夷与汉人同种同质,虽然拥有马和羊群,但还不具备草原牧民的特点。最简单例证便是,当时被称作蛮夷的部落都是徒步作战,而“抵御入侵”的诸夏则已以车代步。他们与诸夏一样也从事农业耕作,只是水平较低,不得不兼营其他混合经济,拥有相对较多的畜牧而已。[7]
对早期史籍记载的“蛮夷侵夏”,拉铁摩尔也有异义。他认为所谓“侵略战争”,并非少数民族蓄意进攻,背后根源是汉地社会的扩张。他以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为例,期间诚然有少数民族的压力,但正是秦部落在泾渭流域的崛起,迫使居于山陕的戎族迁出旧的聚居地,向南部、东南部移动,加剧了与周王室的冲突。其后,周王室固然退出关中平原,但秦却继承了广阔的空间。[8]正是由于日益发展的农业文明的挤压,被迫退却的部落进入草原,并与走出森林来到草原的原始民一起,发展出了适合特定环境的生活方式。
其二、农耕、游牧互动的边疆
自汉兴,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持续南下对汉地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胡汉对峙的模式一直延续到近代,保境安民是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的重任。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社会的关系,也是边疆史研究重点之一。但在传统的研究框架中,往往以汉地社会为本体,而作为另一方主体的游牧社会,成了客体对象,甚至被某些研究者当做带有蛮夷色彩的“边患人群”。但是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打破了这种以中原农耕文化为本体的传统研究模式。他认为,正像专门化的农业文明一样,游牧文明也是畜牧经济高度专门化的产物,二者并无优劣之分。中国的边疆问题源于汉地社会的农业文明和草原社会的游牧文明的交汇、碰撞与冲突。正是二者的互动,构成了边疆纷争的主要矛盾,而并非因为游牧民族的单方面闯入汉地社会。因此,他恢复了游牧民族在中国边疆矛盾冲突中的主体地位,采用平视视角,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互动中,更为客观、公允地重构中国边疆的历史。
作为一种优势的文明,农耕文明自产生之后,就向外有选择地扩张,先是顺黄河进入中下游大平原,而后向南淹覆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南,虽有大片亚热带雨林但这里河网密布,一样适于建立中原模式的精耕灌溉农业,只不过由旱作农业改为水田农业而已。因此,南部边界是一种可以发展同质文化的“软”边界,只要解决好规模扩张后的管理问题,农耕文明的南拓就会不断地向前延伸。然而,向北的扩展却遇到了障碍,“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迥异的地理环境是一种只能发展异质文化的“硬”边界。[9]越界的汉人想要生存,就必须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农业基础的丧失意味着汉地社会的一切规则失效,这便违背了扩张的初衷,汉人只能在草原边缘止步。
如同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民往往被汉地文化同化一样,进入草原的汉人也一样会“入乡随俗”,可见同化并非文明孰优孰劣的问题,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草原边缘,人们必须放弃精耕灌溉农业,丰歉依赖降雨,经营只能靠增加土地面积获取更多收成的“广种薄收”农业。向北,依赖混合经济比单纯的粗耕农业更为安全。而再向北延伸入草原内部,畜牧成为基础经济形态,一种完全不同农耕文明的草原生活方式和游牧社会秩序,在这里确立。随着社会大批人群和畜群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草原最终形成自己的社会体系。于是,沿着蒙古草原的边缘,两种文明、社会对峙形成,“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0]
然而,这种对峙局面并不意味二者彼此间绝缘,不能完全自给自足的游牧社会对汉地社会有着极大的依赖性,牧民的生产、生活资料大都需要从汉地社会获得。而汉地社会,基本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有着内在封闭性,人口和财富的流通被严格限制,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加上游牧社会财富积累困难,基本不具备购买力,使得正常的贸易渠道不能获得所需,于是便铤而走险,试图依靠入侵、偷袭等武力手段获得,而游牧骑兵的机动性又使其在冷兵器时代拥有了较大的优势,边疆多战事由此成为一种交流的常态。通过对农耕游牧文明产生、演变和互动过程的梳理,拉铁摩尔尽可能地还边疆历史场景以真实。
其三、对长城的认识
及至今日,在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背后,长城又往往被视为封闭、保守的象征,甚者又认为其未能起到抵御草原铁骑的入侵,纯属劳民伤财之举。而拉铁摩尔却从另一角度诠释了长城的意义。在他看来,长城的建立,并不由于草原游牧民的入侵,而是汉人自己试图在定居农业与游牧部落之间建立一个永久的文化分界线。[11]长城的最大功能,就是区分了两种文化类型: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
众所周知,秦于商鞅变法崛起,始皇帝连年征战抹除各国边界,扫除六合,混一宇内,置整个华夏社会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之中。然而在草原边缘,他却止住了拓疆开土的步伐,下令修筑万里长城。对于修筑的原因,普遍认为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入侵。拉铁摩尔却认为这一观点难以找到史实支撑。因为在先秦的史料中,并没有找到如汉代般的边疆危机的记述,甚至草原游牧铁骑大肆掠境的记载也很少见。相反,史料所传达的却是另一意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12]《汉书·西域传》也记:“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13]文字传递的信息实际是秦始皇为廓清地域,而主动出兵“攘却戎狄”,将他们逐出宜耕土地。因此,在拉铁摩尔看来,于汉地、草原之间修筑长城,是汉地社会内部自我进化的结果,而非源于草原游牧民对汉地社会的压力。对秦而言,“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一个固定的边疆,包括一切真正适宜中国的东西,隔绝一切不能适合中国的事物,长城就是这种信念的表现。”[14]
不仅如此,拉铁摩尔还认为长城
“不仅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15]帝国既用长城阻止少数民族来自长城之外的攻击,也不自觉,却相当努力地阻断了帝国内部任何分子想要飞出汉地社会投向草原怀抱的图谋。对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增加财富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从事精耕农业,并限制人口和财富的流动。而对于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农民而言,他们面对着汉地社会和草原两个市场,而且后者又往往有着更大的利润。他们的事业,不论其为农为商,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贡献要比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更大。因此,边疆社会显示一种危险的离心倾向。长城的修建,在拉铁摩尔看来,就是试图阻止这种趋势的产生。[16]
然而,这条防御性的,用以隔绝草原游牧民的帝国界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拱卫中原王朝,但这种排斥的态度也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反而加速了草原游牧社会的形成。到汉代,游牧社会已强大到足以威胁汉地社会。边疆地区的两个社会旷日持久的冲突自此全面开启了。
[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特点及对其的评价
作为拉铁摩尔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也集中体现了拉铁摩尔在治学方面的独到之处。费正清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欧文展开他丰富的想象力,把观察结果同已知事实相结合,建立起了历史理论的城堡。无所成就的汉学家们可能会嘲笑他,可是他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堪称是一位蒙古问题专家。”[17]这个评价很中肯的点出了本书的研究价值和地位。如其所言,重视实地考察是本书也是拉铁摩尔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或许是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的教育,使他摆脱了条框的束缚,在不断的行走中,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这是那些“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的研究者所无法比拟的。如其回忆中所说:“我对中国、蒙古、中亚的知识并不受什么人的影响建立,而是靠在遥远地区的游历获得。我学习汉语、蒙古语,直到我能读能说并完全脱离翻译。我在商人、商队成员、士兵、土匪、农民、牧人、地主、谷物商人和其他人之间平等地交流旅行……正是这样真实的生活基础,使我建立起地理、历史与社会研究的框架。”[18]广泛的游历使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拥有了中国边疆史的发言权,道人所未道,完成了自己在边疆研究中的突破与创新。此外,他本身所具有的西方教育背景,中国成长和工作经历,在英国、瑞士、蒙古、阿富汗等地的游历,使其文化视角趋于多元。而这种多元的文化视角又使其在考察和评价历史问题时,避免了单一文化模式的思维,在摆脱带有民族感情的局限和偏见的立场上,更为客观和公允地对待历史,并且置历史问题于一个更为宏观的背景中分析其影响。比如他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思考中国边疆冲突,从而摆脱传统的汉地文化本位的视角,从双方的互动中还原历史的真实。
但是,过分地强调实地考察,较少在理论上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作品的学术性。这一学术弱点“有时就被那些想诋毁他的人们贬低为非学术。”诚然,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考察和调查的实证研究,对理论不感兴趣,致使其作品的理论色彩不浓,缺少缜密的逻辑性,但说拉铁摩尔的著述缺乏学术性是不中肯的。此外,拉铁摩尔运用边疆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规律固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视窗,但是过分夸大边疆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简单地把向外扩张和边疆移动归结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值得商榷的。[19]
无论如何,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国学者是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特别是他在书中终始贯穿的对中国内陆边疆历史传统阐释框架的颠覆以及在多元文明互动中重构中国边疆历史,之于我们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分析。
《大航海时代中的十字架》《世界汉学》2006年
第1期;《“E-考据时代”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以瞿太素及其“家难”为例》,收入古伟瀛主編《东西交流史的新局:以基督宗教為中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从韩霖《铎书》试探明末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清华学报》(台湾新竹)2004年新34卷第1期;
《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天主教徒韩霖投降李自成考辨》《大陆杂志》(台北)1996年第93卷第3期;《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96年第26期;《明末中西文化冲突之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國为例》《第一屆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世变、群体与个人》(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瞿汝夔(太素)家世与生平考》《大陆杂志》(台北)1994年第89卷第5期。详见黄一农个人网站:http://ylh.theweb.org.tw/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