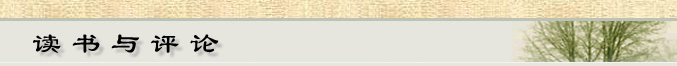明清史研究中的整体性视野考察——读《明代的变迁》
东北师范大学
亚洲文明研究院2007级硕士生
肖金
[提 要]
《明代的变迁》一书围绕“明清社会变迁趋势”这一基本问题,考察这一时段的历史在不同层面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回应,最后提出“帝制农商社会”的结论。正是由于有各个具体问题与基本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照,才使得跨度二十余年对不同的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都在指向同一基本问题,从而在逻辑上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关键词] 历史;
变迁;
整体性
历史文本是文明实现其记忆保存的基本形式。文明记忆的保存,一方面可以使一个文明体自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获得延续性;另一方面,也为文明体能够具备一种自省意识提供了条件。前世之治乱兴衰不远,可以为后事之殷鉴。《春秋》之笔削褒贬寓于一字,《史记》之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传统的历史文本的书写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并在其内容上表现出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势关注。国家政治在历史文本书写的内容主体中的强势,直接导致了传统史学视野的局限。
西方近代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新史学就是在对于传统史学的文本选择与叙述视野的局限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之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史学拓展了文本的选取范围,将理性(科学)精神和进步理念引入历史书写过程之中。理性(科学)精神使历史叙述专门化,并在理论意义上将历史进行了层次性划分,从而实现历史学的专业分工。专业分工使历史叙述可以通过多维视野更接近历史存在本来的复杂性,同时也可能导致试图以单一视角、单一维度把握历史变化所造成的对于历史真实存在的整体性的割裂。进步理念使历史叙述走出了传统史学所描述的治乱兴衰更迭相替的循环模式,试图建构一种依赖于人的理性自觉、以发展为本质的、具有乐观情怀的历史逻辑。然而,当进化观从生物学领域走入社会学、历史学领域,在人们潜移默化中将其视作具有先验性的历史本质以及历史叙述中的价值尺度的时候,它同样可以把我们引向对于历史变迁解释的简单化、线性化的因果逻辑的歧途。更令人悲观的是,对于由理性精神与进步观念所建构的文本和话语模式率先持质疑态度的后现代主义者,似乎也面临着破而不立的尴尬。文明史观是现代历史学叙述模式之一,自然也不可能完全回应现代史学面临的所有问题,作为历史叙述的切入视角,其意义在于能够比较有效的展现历史变化的整体性。
历史研究中问题决定视角,其小者,须得显微镜方能见其精细处;其大者,则非望远镜不能窥其全貌。《明代的变迁》一书正是运用这种显微镜加望远镜,历史观察中长短镜头相结合的方法,围绕“明清社会变迁趋势”[①]这一基本问题,考察这一时段的历史在不同层面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回应,最后提出“帝制农商社会”的结论。正是由于有各个具体问题与基本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照,才使得跨度二十余年对不同的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都在指向同一基本问题,从而在逻辑上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一、基本内容
1,国家.社会(群体/阶层).家庭.个人:历史变迁趋势在其不同层面的映射。
关于国家层面的讨论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中“国家宗教管理”、“城隍祭祀”、“国家祭祀体系”放在国家制度层面来讨论的时候,就不仅是一个信仰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货币制度的演变”和“财政危机”则是从经济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化及其成因。
《明太祖的国家宗教管理思想》讨论了明太祖在制定国家宗教管理政策过程中的思想具有的现实性:对僧人和道士有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并禁止游离于国家政治权力范围之外的各种邪教和巫术;实用性:利用释道引导乡愚、阴赞王纲之功,并有限制的优容边疆宗教;包容性:儒释道三教体用相济、经权相交。从有利于国家政治实践为出发点制定的具有弹性的宗教管理政策,随着国家对社会控制力的削弱,宗教问题社会化,一方面“于民间文化增加了活跃因素”,[②]同时“对国家财政和社会秩序则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③]《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探讨了国家祭祀的对象及其国家政治、社会观寓意;祭祀体系与祭祀活动的变化与国家秩序的整体状态的关联。儒家思想所主导的反映以天权为核心的天、神、君、民的秩序观念的国家祭祀体系,[④]本身依赖于现实政治权力(皇权)的参与,而在佛教、道教和民间杂神崇拜信仰的冲击影响之下,现实政治权力(皇权)往往又成为既有体系直接的破坏性力量。《明初城隍祭祀制度》是一篇商榷性文章,主要是厘清滨岛敦俊《明初城隍考》所论洪武“三年改制”说中对于历史材料的误读及其论证过程中存在的以明中后期情状反推明初情状造成的理解混乱。与《明后期太仓收支数字考》一样,作者传达的是一种立足事实,不轻信、不盲从的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讨论的是作为明代特有的国家政治权力中枢的运作机制和模式的票拟制度的形成和演变趋势,及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来自官僚体系内部的挑战:权臣操柄、阁员卸责;来自皇权的挑战:皇帝猜疑;来自宦官集团的挑战:宦官专权),而票拟制度运行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极端皇权专制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体制性因素造成的。
《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考察了以货币白银化为核心的明代国家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对传统社会经济关系、政治社会体制、国家财政体制、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影响。作者同时指出,白银货币化过程虽然冲击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并为历史走向的转变(主动的融入世界资本贸易市场)提供了可能的契机,但历史走向的转变终究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任何单一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力都是远远不够的。《论明末财政危机》考察了明末财政危机的表现和特点(附《明后期太仓收支数字考》)。作者透过明末财政危机的种种表象,指出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国家财政体制从实物向货币转变所造成的四大矛盾:财政体制变化与原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冲突;与原有政治经济地理布局的冲突;与原有军事制度的冲突;与明中叶以来中国货币关系的急剧变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冲突。与白银货币化一样,明代货币财政体制也是一种被动的、受迫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关于社会(群体/阶层)层面的讨论主要涉及了历史变迁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模式;下层民众的价值观取向及其信仰世界。
《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沉沦感》讨论了晚明知识分子群体面对社会变迁试图做出回应时陷入的困境,从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与社会变迁的矛盾分析入手,指出其只能在道德复古中寻求振作的悲剧性命运。《山人与晚明社会》与《儒家传统与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讨论了晚明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生存状态和社会行为的转向,在儒学的进一步社会化过程中,多数士人浸润于流俗,见证并参与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
《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针对余英时和韦伯在讨论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变与传统儒家伦理关系时在视角选取上对下层社会宗教和伦理价值的特殊性忽略,相对于韦伯认为的儒家思想伦理观念对于社会的商业化转型具有阻碍作用和余英时认为的儒家思想伦理观念与社会的商业化转型相契合,作者给我们提示道:虽然传统儒家思想伦理观念对商业发展是持抑制和否定倾向的,文化精英阶层仍然以“步入仕途”为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最高取向,但是主导晚明社会商业化转型的并不是文化精英阶层而是下层大众。不是儒家传统的思想伦理观念,而是下层大众从生活实践中对利益追求的本能出发形成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与晚明社会的商业化转型趋势具有一致性。《17世纪前后中国北方宗教多元化现象初论》讨论儒家思想占据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况之下,北方下层民众的信仰世界的多元化特征。作者认为,儒学的嬗变的延续、晚明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混乱、明后期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以及从而导致的国家对部分领域控制力的削弱,都是这个时期北方下层民众的信仰世界呈多元化特征的社会基础。
关于家庭层面的讨论主要涉及了“下层社会家庭伦理实践与儒家家庭伦理的关系”;通过解读当时文学文本中包含的历史寓意,进而分析“悍妻”现象与妾制在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
《儒家思想与17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注意到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家族共居”、“孝道”、“贞节”、“夫权至上”等观念在下层民众的生活实践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忽视或挑战。作者分析这种变迁的社会文化因素是:12到15世纪以来占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学,在思想层面遭到了16世纪由理学进一步嬗变而出现的心学的挑战。考虑到下层民众普遍的知识认知水平和生存状态,更成为他们实践儒家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障碍。[⑤]《“悍妻”现象与17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妾》主要是以《醒世姻缘传》为文本对象,并从中抽离其具有真实性的历史寓意,考察17世纪中国家庭中“夫妻”、“妻妾”关系出现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传统家庭制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某种松动。凝固的成文的家庭法规往往会掩盖了现实具体实践中的家庭生活的差异性,作者指出:“所有成文的社会规范都是为了否定和约束人们的某种行为的,因而它的反面可能具有很大的真实性。”[⑥]
关于个人层面的讨论涉及的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黄宗羲思想三议:读<留书>札记》考察了黄宗羲的“民族思想”、“民主思想”、“对明末党争的认识”,其思想中的这三个部分内容,正好是其个人思想对于其所处的文化传统与所经历的历史变迁的直接回应:其民族思想来源于元朝民族统治的文化记忆、满清新政权带来的亡国之痛以及儒家传统文化的华夷之辨、华夷之防。其“民主”思想来源于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本”、“封建”观念的继承和重述。其“对明末党争的认识”是对明王朝崩溃的直接反思。如果没有新的、外来的观念的影响,一个人想要脱离自身时代实现对于传统的完全超越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黄宗羲对于过去历史变迁的反思和对于未来政治的设想,都只可能通过儒家传统政治文化所提供的话语理念与思维模式来进行表述。
2,历史的变迁与文明体的自律。
西方话语支配下的现代历史叙述和解释模式林林总总,对于中国历史这个客体,并不缺少冷峻的客观,反而需要的是应该多一点体认的热情。对本书结论章题目——“明代历史的自律”的解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样一种决心:尝试重新审视明代中国文明的自我运作机制。
全书第五部分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看法》与《“大分流”还是“大合流”》两篇论文,可以被看作结论章《明代历史的自律》的方法论检讨的补充。《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看法》是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厘清“封建”概念的三个不同涵义。指出将“封建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化以前历史阶段的性质概括,同时也就产生了诸如“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本身存在逻辑陷阱的问题。实际上作者在80年代末就已经在《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一文中质疑了将“封建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化以前历史阶段的性质概括的合理性。《“大分流”还是“大合流”》针对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的“欧洲核心区和世界其他地方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的观点,[⑦]在肯定其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同时,指出论证中存在的:与“内卷说”一样以经济学视角解释历史现象从而造成的事实服从于理论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区域研究的可比性问题。结尾部分,作者分析了运用文明史观解释明清历史趋势的可行性。
结论章《明代历史的自律》是对于全书所关照的“明清社会变迁趋势”这一核心问题的直接论证和表述。第一部分:“方法论”,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明清史研究中遇到的由“封建社会晚期”这一预设式的社会形态定性所导致的一系列理论误区和逻辑陷阱问题,而这一预设产生又是在包含了对于社会发展五形态图示的盲目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历史进化同步性假设等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支撑中国传统历史具有自律性,作者还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形态孕育障碍说。(文明体内部稳定成型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心理,在不遭遇他文明的冲击的情况下,将会保持一种持续的惯性,文化自我变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部分:“变迁”,作者首先界定所谓历史的变迁必须具备“新异性”与“不可逆转性”的特点,从而指出明代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新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的简单化;市民文化的活跃;人口爆炸;儒学社会化七大变迁,而这些都是中国文明体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既不同于过去又不同于西方的具有持续性的新特征。
第三部分:“帝制农商社会”,明代中国历史有上述变迁的一面:变迁冲击和改变了原有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比如社会商业化程度加强等;作为一个具有自律性的文明体,明代历史更有继承的一面:比如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组织结构仍旧在惯性中保持下来。
二、余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们面临着一个新的环境。以往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以政治、经济作用关系为基本视角的历史叙述,转向了历史真实中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对于历史的微观解释似乎也比以往的宏观把握更具有生动性和真实感,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基本历史问题(比如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质中的所谓“封建社会”问题),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回避了。一方面是在研究对象中对于这些问题的回避,另一方面,在对于具体的历史问题的研究表述中,又将那些只在政治上正确却未必合乎历史真实的论断,作为无需置疑的一般性概念使用着。本书所收录论文的时间跨度中记录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省过程:从80年代末作者开始对于将“封建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化以前历史阶段的性质概括的合理性的质疑,到对于明清历史趋势做出的“帝制农商社会”的论断的提出,在作者整个明清史研究体系中形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脉络。“帝制农商社会”虽然是作者在明清史研究中提出的论断,而这个论断的意义又将不拘囿于明清史本身,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整个中国传统历史同样具有启示性。
我们的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在对于历史基本问题的回避和默认的态度中因循迁延,寻求历史碎片的真实,走一条支离之路;一是拿过西方既成的历史分析的话语模式和结构,寻求中国历史中与之印证的材料,走一条覆蹈之路;一是重新评估中国历史变迁具有的不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体系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走出一条新的路来。最后这条路自然是充满艰辛,却是代表了未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可能出路。《明代的变迁》在这条路上为我们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