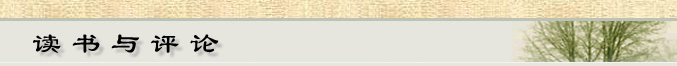诗经·名物·新证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2008级博士生
谷丽伟
[提 要]
在传统经学消亡的今天,学者对于“六经”原典的解读,由于现代学科分工体系的影响,出现了文学和历史学的分野,如此一来,固然各取所需,却也必有所失。《诗经名物新证》给我们展现了一条从文学叙述中寻找历史真实存在的途径。
[关键词] 诗经;
名物;
新证
最近读扬之水[①]《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内容图文并茂,文笔灵动,读后颇使人耳目一新,我们也得以从诗经、名物、新证三个词中寻绎作者的意图所在。
《新证》是扬之水早期的作品,作者从名物入手研究《诗经》,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名物研究,所以称之为“新证”。《诗经》三百零五篇,作者只选取了其中的十数首进行疏解。《新证》一书中各篇本是相互独立的,“写出第一篇《秦风·小戎》之后,便开始在《中国文化》连载”,[②]但作者在疏解具体诗篇之前的总论,将各篇连结为了一体。诗以言志,诗是用来表达心意抒发感情的,所以诗首先是文学的,但诗终究不能脱离产生它的时代,所以诗又是历史的。扬之水是想由名物而考证诗义,进而考察历史,“文字考据的同时,更援实物以证,并因此揭出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并因此使物与诗互为映照、互见光彩”。
然而,今日的诗学已经远非诗三百篇产生之初的本来面目,作者由名物而历史的意图难免会遇到一些难题,诸如如何看待《毛诗序》,如何解释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等等。作者在总论中回顾了诗学建立的过程,也表明了自己研究诗经的态度,“力求持平实的态度,鲁、齐、韩、毛,四家皆不偏废,于汉,于宋,于义理,于考据,于‘载道’,于‘缘情’,凡以为合于诗义者,皆取以为用,总欲‘揆之情理,参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诗人之意。’”[③]
作者在总论中又援引诗篇将周代从兴起、迁徙到兴盛、衰落的大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先祖后稷善种植(《大雅·生民》)、公刘迁至豳(《大雅·公刘》)、古公亶父迁至岐山(《大雅·绵》)、文王作丰武王都镐(《大雅·文王有声》)、西周的衰落(《大雅·民劳》),“诗虽然不是一部编年史,但它略略点画出来的兴衰演变之迹,足可以教人把它当作史看了”。[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周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武力经营四方,作者在总论中写《周南》、《召南》时顺势提及了这一点,第一步是征服西方,第二步是伐东夷、靖东国,其后是召公(奭)对南土的经营,而《周南》、《召南》即南土之乐。
历史的大场景已经布置停当,历史中的细节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作者对《诗经》中十数篇的疏解便是总论这个纲下的目。
扬之水也从《诗经》的名物写起,但她和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同,后者只写鸟兽草木,或许孔子的时代车马、旌旗、天文、地理皆是耳熟能详之物,而对于我们,无论是诗中的鸟兽草木,还是旌旗、衣饰都已经脱离生活日用了。扬之水不仅仅局限于名物的释义,她笔下的名物更像一座座桥,横贯古今,读者就经由这桥走进诗人的思绪,走进诗人的时代。扬之水的《新证》新在利用出土实物与名物的验证上,以前的学者做名物研究,不免纸上谈兵,扬之水却能探访周原遗址,观摩出土的一件件器物。而且古之学者已经把诗解释的很透彻了,扬之水需要的是挣脱《诗序》的束缚,甄选出最合理的解释,然后辅之以出土实物。兹举作者疏解《秦风·小戎》中“四牡孔阜,六辔在手”中的“六辔”为例,“六辔”常见于诗中,如“六辔耳耳”(《鲁颂·閟宫》),“六辔如琴”(《小雅·车》),“六辔沃若”(《裳裳者华》),四匹马应当有八辔,为何诗中只提及六辔呢?作者结合出土的战国刻纹铜器,发现“两骖马的内辔乃系结于相邻之服马的衔镳处,而两服马的内辔尚须在辀前交叉一次,……故持在御者手中的,便只有六辔”。[⑤]作者在详细解释之外又配以图示,如此读者自可恍然大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证》倒符合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过,孔子授诗,多识鸟兽草木只是习诗的额外收获,扬之水所要索隐的点滴历史却都在鸟兽草木之中,孔子是让弟子博雅,扬之水是玩味历史。
《新证》仅疏证了十六首诗,且篇幅多集中于大、小雅,但作者却别具匠心。《大雅·公刘》、《緜》记述了周先公公刘、大王为周王朝的发展、兴盛做的奠基工作,先周时期周民族迁至豳又迁至岐山,其居住、生活情形大略可见;《七月》追忆一年的农事,《大田》详述稼穑的黍稷和工具,《斯干》极力状写版筑之法及建筑风貌;另外,《楚茨》写祭祀场景,《宾之初筵》写大射礼仪,《秦风·小戎》、《郑风·清人》、《大雅·韩奕》写车马旌旗制度,《小雅·鼓钟》写鼓钟音乐,《小雅·都人士》、《鄘风·君子偕老》写时人服饰,《小雅·大东》写天文、星象。扬之水力图通过这十数首诗的名物新证,把整个周代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她先粗笔勾勒出先周民族的筚路蓝缕,周民族的兴盛,郁郁而文的周代礼制、周王朝的渐衰,接着她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的画面中,带我们去细处看丰收的禾稼、质朴的先民,看狩田的车马、猎猎的旌旗,还有夜空中闪烁的繁星。
了解了《新证》一书的体系内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本书的价值呢?还须将其放在诗经学史中进行考察。
《诗经》又称“诗三百”,自从结集以来,一直深受学者重视,只是由于各个时代政治环境或者学风的迥异,受重视的原因各有不同。先秦时期,儒者如何授诗,今天已不可得而详知,我们只能从先代圣贤的言论中略窥一二: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同上)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孔子认为诗可以用来表达兴观群怨的情怀,温柔敦厚的诗教使人明晓事父、事君的道理;诗又可以文饰言辞,出使四方,应答专对,《左传》外交场合的引诗赋诗正反映了诗的这一功能。关于“诗言志”,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始于荀子,可当我们分析了孟子的“以意逆志”后,便会觉得这一论说值得商榷,孟子用“意”所逆的“志”不正是诗所要言说的“志”吗?应该说,“诗言志”的观念来源甚早,并不仅仅始于荀子。孔子讲授《诗》,或许是讲解诗篇的作意,诗中个别字句的道理,诸如“白圭之玷,不可磨也”。同时,出行又免不了教弟子们识别田野中的鸟兽草木,这些名称常常出现于诗三百篇之中。另外,诗三百篇原本是皆可配合乐调演唱的,但《诗》的乐调应该不是“六经”之一的《乐》书,荀子在《劝学》篇便将两者分明了,“《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乐》之中和也”。《诗经》风、雅、颂三体的演奏方式当时应没有记录,只有乐官身守技艺而已,战国时期,新乐盛行,乐官改习新乐,《诗》便与音乐分开,只剩下了文字。
“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末期,诗被引用的场合渐渐少了,士人似乎不在乎“言而无文”,而是忙于周游列国,朝至秦而暮至楚。再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国与国的较量凭借的是军事经济实力,对《诗经》的研习自然少了。秦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王朝虽短命,造成的文化凋敝局面却至汉初六十年间犹未改观。诗三百篇因为不仅仅著于竹帛,虽遭秦火而讽诵如故,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诗经》在汉代是否有今古文之别是值得思考的。然而秦火仍有影响,汉代源流错综的四家诗传授系统便说明了这一点。起初齐鲁韩三家诗盛行,继而三家衰落,毛诗渐起,至郑玄为毛诗作笺注而毛诗独尊,说解诗篇作意的《毛诗序》后来成了学者聚讼的对象。
从诗三百篇到《诗经》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蹊跷,诗三百经历了怎样的坎坷而脱胎换骨?这是古往今来研究诗三百篇的学者共同的迷惑。《小雅·楚茨》本是详述祭祀场面的,《诗序》却云:“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君子思古焉。”《荀子·大略》篇云:“小雅不以於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难道《毛诗序》是有道理的?诗人作《楚茨》正是思古往之祭祀场面而疾今之政吗?或者《诗序》是受了荀子此言的启发而如此这般地讲解《楚茨》?
《诗序》解诗几乎篇篇有所指,但很多情况下诗的内容似乎与《诗序》相悖或者毫不相干,诗人远逝,三家诗著作也大多亡佚,《诗序》这桩公案在学术史上聚讼纷纭,学者也在存序、废序中争得面红耳赤。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毛传、郑笺更成了解释《诗经》的唯一权威。宋人有疑经风气,欧阳修《诗本义》、郑樵《诗辨妄》、朱熹《诗集传》皆对《诗序》持怀疑批评的态度,然总的来说,欧、朱二位对《诗序》很多还是信服的。清代学者小学功底深厚,辑佚之风又大起,拥护毛诗的便著书阐发毛义,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拥护三家诗的也不遗余力搜罗三家诗遗说,如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当然,学者对《诗经》的研究也不限于诗序,有对诗三百篇的作者、《诗经》的结集年代、诗与乐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也有对诗篇中所涉及的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专题进行研究的。举其要者,有魏晋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清包世荣《毛诗礼征》和朱濂《毛诗补礼》、清洪亮吉《毛诗天文考》、清朱右尊《诗地理征》。清代也不乏从文学角度研读《诗经》的作品,如方玉润《诗经原始》。
五四之后,受西学的影响,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立志拨去诗篇上所附的《毛诗序》的荆棘,还诗三百篇原来的乐歌面貌。胡适曾试着作《诗经新解》,用白话文解释诗篇,但用西方的思维解释传统的《诗经》,未免有些不相宜。当代学者多视《诗经》为文学作品,《诗经》译文也蔚然成风,然而押韵古朴的诗篇一旦成了白话文,诗的意蕴也随之稀释了。史学家更注重雅、颂中的史料,以诗证史,然而诗篇的整体之美就成了“支离疏”。
孔子的时代,诗是鲜活的,不仅可以讽诵,还有实用价值,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文本,谁能透过历史从文本中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呢?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而诗三百篇,正如扬之水在《诗经名物新证》中所说: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新证》一书,既保留了诗篇原有的文学元素,又不乏历史的真实,对于《诗经》的研究应是必要的。
寻觅优美诗篇背后的西周历史,扬之水清新灵动、诗韵四溢的文笔后面应有这样的思绪,在《后记》中,写到踏访周原,无疑也透露出她这样的雅意。当她漫步或驻足于某一青铜或玉质器物前时,不免生出“折戟沉沙铁未销,试将磨洗认前朝”之感吧。
[①]
扬之水:原名赵丽雅,曾任《读书》编辑,后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等。
[②]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第5页。
[③]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第9页。
[④]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第19页。
[⑤]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第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