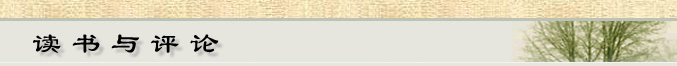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与微观史学的结合
——
读《蒙塔尤》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级本科生 徐晴
[提
要]《蒙塔尤》一书中,作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运用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史的视角,通过对蒙塔尤这个小村庄中林林总总的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分析,为我们揭示出最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中优秀的代表作品之一,但其中暴露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本文仅对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一点自己的理解。
[关键词]《蒙塔尤》;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微观史学
《蒙塔尤》描述的是1294—1324年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尼地区一个叫做蒙塔尤的小山村中两百多名农民的生活状态。作者通过对当时卡尔卡松宗教裁判所在当地的法官——雅克·富尼埃主教为追查纯洁派异端和非正统天主教徒而对村民们进行审讯时所做的记录簿进行整合和分析,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面貌。材料弥足珍贵,但整理和分析的方法更加值得注意。
一、历史人类学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作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史学家们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被称作“年鉴——新史学派”。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着重于研究各种变化缓慢但影响深远的事物,例如人类的生活状态。
人类的生活状态,也包括其社会观念、风俗习惯、内心情感等等,这都是人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因而年鉴学派新史学理论的这一倾向必然导致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年鉴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曾预测:“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也明显体现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意图。
在书中,作者首先考察了“蒙塔尤的生态”,从它的自然环境,如土地状况、农作物、牲畜情况,到社会环境,包括人口、房屋、家庭关系、劳动分工、货币、交通、饮食、疾病等各个方面,再到其几种政治权力集中于一处、相互制约的状况,给予一个宏观的概述;而后在其第二部分“蒙塔尤考古”中,详细地、分别地介绍了村民们的家庭观念、社会关系及宗教思想。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框架,包括语言、婚姻家庭、居住方式、亲属关系、宗教信仰等等,而《蒙塔尤》的内容几乎涵盖了这些所有的方面,或者也许作者就是依据着人类学的框架来构建本书的体系的。
另一方面,勒华·拉杜里在材料处理中还充分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心态史学的研究也是对长时段理论的一种发展。它以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即研究一个群体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的、惯性性的行为。我们知道,富尼埃主教的记录簿中的资料实质上只是一些村民们相互告发时的“闲言碎语”,而作者则将这些话语中所描述的支离破碎的事件整合起来,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事件背后的思想,考察村民们的心态,如爱情、对儿童的感情、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时间和空间的观念、金钱观、家庭观、命运感以及宗教情感等等。勒高夫评价说:“今天他(勒华·拉杜里)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
《蒙塔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历史很好的方法,许多人在研究心态史、历史人类学方面是以它作为榜样的。可是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蒙塔尤》的形成具备了太多的特殊条件:其一,雅克·富尼埃主教是一位“极善于弄清事实真相”的法官,在他审判时,被告们往往被要求描述“大量的日常‘生活片段’,以此来支持和证实他们的供词”。主教的这种“细节癖”以及事必躬亲的做法使得“除了信仰和异端以外,他还揭示了社区的生活本身”。其二,富尼埃主教有意地“为他在帕米埃宗教裁判所取得的成就留下这份证据”,而他本人后来又成为教廷的主宰——伯努瓦十二世,这一显赫的地位使得他所做的这份记录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较多的关注:记录簿被收藏在梵蒂冈的图书馆,并且在勒华拉杜里之前已有不少人对这份材料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这些特殊条件大大降低了这种史学研究方法的普遍适用性,换句话说,一种好的方法已经提出,却期待着我们去挖掘更多适用它的材料,或者是寻找更多获得类似材料的途径。
二、微观史的视角
人的个体意识虽然由来已久,但它在历史领域内的影响却很迟滞。在传统史家的笔下,普通民众总是千篇一律的面孔,他们就像是漫画中的简略画法,象征性的头,象征性的身体,象征性的甚至不齐全的五官,没有表情,他们通常只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对于个人的重视则局限于“精英史”。但微观史学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局面。
在《蒙塔尤》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个性观念。每个村民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但是在作者笔下,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虽然平凡无奇但详细无比的事迹,有自己丰富的内心情感:每一个个体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当然,作者不可能对每个村民都详细地论述,但我们还是能够对其中很多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好心的牧羊人”皮埃尔·莫里,本堂神甫皮埃尔·克莱格,还有他的情妇、女贵族贝阿特里斯·德·普拉尼索尔。就像文学作品的创作强调“人物塑造要有个性”一样,然而历史记述中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原本就是有个性的。)
微观史学的一大特点便是贴近生活。阅读《蒙塔尤》会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一个小小的村庄,居住着几十户人家,他们每天吃饭种地聊家常,他们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就和我们一样,这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历史。
书中的内容涵盖了这个小社会群体的各个方面,但是有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异常高,那就是“家”和“异端”。
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是作者论述的重点问题。在奥克语中,“‘家’一词具有住所和家庭不可分割的双重含义”。作为前者,一个家的核心部分是厨房,“人们在这里吃饭,在这里死去,在这里接受异端、交流内心的秘密和村里的闲话”。作为后者,家则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核心,“在情感、经济和门第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信仰的转变常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男子对女子的爱也会延伸至她的整个家族,“我热恋着她,因此我爱她的家”。
家庭的观念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婚姻的观念。在蒙塔尤,未婚男女同居是很普遍的现象,探究其原因,会揭示出这样一种观念:“结婚是不能轻易实现的事,他要求欲婚者对未婚妻怀有爱情,而且如有可能,他们还希望或多或少从女方那里得到一笔作为陪嫁的财富。‘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还有信仰是否一致的问题。面对这些严格条件,许多蒙塔尤人更喜欢选择姘居这种流行的简便方式,至少在开始时如此。”婚姻也是这一地区等级观念唯一得以体现的地方:尽管蒙塔尤人对于社会等级的观念很淡,但一旦涉及婚姻,它便会变得十分严格。一位女贵族可以找若干名农民情夫,但“绝不会下嫁给一个平民百姓,她只会嫁给贵族,至少是教士”。这些丰富的材料都使得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那个时代法国农民的家庭生活。
第二个关键词是“异端”。富尼埃主教的主要任务便是追查异端分子,因而信仰问题也占据了书中的大量篇幅。
蒙塔尤村被称作“佩戴黄十字标志的村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异端学说盛行的地方,异端派教长在这里频繁出没。可是我们不能因此一概而论:在这里既有纯洁派的坚定信徒,也有笃信天主教的“本分人”,但更多的人都“脚踩两只船”。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便是皮埃尔·克莱格。作为本堂神甫,他本应是罗马教皇和堂区主教的代表,然而在各个方面,皮埃尔都显示出一个纯洁派教徒的身份;作为具有异端倾向的克莱格家族的一员,他却在母亲死后将其葬在卡尔内斯圣母殿中圣母玛利亚祭坛旁,以期“让芒加德的灵魂最先享受到从祭坛不断流出的恩泽”。皮埃尔个人的矛盾性体现了整个村落在信仰方面的混乱性。
但是不管怎样,信仰问题在蒙塔尤人的生活中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例如,在婚姻关系中,信仰是关键性的因素:“信奉纯洁教的农民们倾向于在他们之间择偶”,他们“宁可娶一个只有一件衬衣的女(异端)信徒,也不想娶一个陪嫁丰厚的非信徒”。信奉纯洁派的雷蒙·皮埃尔对同样信仰的牧羊人皮埃尔·莫里说:“如果你娶一个与你信仰相同的妻子,你们便可以在家里接待善人们,为他们做好事,还能不冒任何风险地和妻子谈论关于善的知性等问题”,这种说法打动了牧羊人,“和妻子谈论问题,雷蒙描绘的前景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在奥克西坦尼,许多沉默的家庭从不谈论这些问题。所以,这种前景至少是令人向往的”。
在以往研究中世纪宗教问题的时候,依据的大多是那些正统的理论,例如历代教皇的敕令、宗教学家们的著作,而《蒙塔尤》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最基层但也最真实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罗马教廷的那一套理论在民间是如何被人们“信奉”的,以及宗教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
微观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细致化的研究,而这有时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收获,即为历史研究的漏洞提供珍贵的补充。《蒙塔尤》研究的视角是独特的,其所运用的材料也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使它涉及了其他历史研究所没有涉及的一些内容。
例如对于乡绅阶层的记录。作者在研究蒙塔尤这个村落中的权力机制问题时,虽然承认它受到当地的领主富瓦伯爵、罗马教廷及法兰西国王三种权力的共同制约,但他并未将村内机制的运行置于教廷或国家制度的框架中。书中我们常常见到的“统治者”是克莱格家族:哥哥贝尔纳·克莱格是领地法官,代表着伯爵领主一方的权利;弟弟皮埃尔·克莱格是本堂神甫,代表着教皇和宗教裁判所一方的权利。蒙塔尤村实质上是在兄弟二人的共同管理之下,然而克莱格家并非贵族,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世族,他们只是所谓的“乡绅阶层”,蒙塔尤村就是处在这样的“乡绅政治”的统治下。虽然从上层看来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一阶层却在实质上维持着整个村内机制的运转,并充当普通群众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纽带。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克莱格家,客观上为这种乡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再如,它对社会地位向下变动现象给出了生动具体的例子。由于传统史学对个人的关注局限于精英史,因而他们记录的往往是关于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努力或者机遇而逐渐成为精英的,即一个社会地位向上变动的过程。而本书却介绍了不少完全相反的状况:在蒙塔尤,有许多原本殷实富裕的家庭因为信奉异端而被宗教裁判所及其打手搞得家破人亡。例如贝尔纳·贝内,他本来是“可以继承父业、成为产业主的青年人,最终沦为一个受堂区各个集团任意摆布的普通牧民”。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了解到,那个时代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下降时他的生活、心理状况以及他人的态度等。
这些“意外的收获”还有很多,它们可以成为某些专项历史研究的依据,例如礼仪的历史、人的鬼魂观念、成人对于儿童的重视程度问题等等。
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其中不少问题。
关于本书的目的,勒华·拉杜里在前言和中文版前言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寻找关于有血有肉的农民更加详细的和具有内省性的资料”,以蒙塔尤来折射“我们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然而对于这一点,我多少有些怀疑:局部的历史能否真正映射整体的历史?
诚然,蒙塔尤是个最普通不过因而具有典型性的村庄,这里普通农民的生活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一些中世纪后期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可是在阅读本书时我们常常会发现,即使是与附近的村落、牧区相比较,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差异。
以夫妻离异的问题为例。在蒙塔尤,夫妻离异的现象极少。整个宗教裁判所的记录中,“只有一起离婚事件和一起以离婚相威胁的事件”,而这两起事件都源于双方信仰不同,且都是男方主动的。可是我们能否就此判断,中世纪欧洲家庭生活中,离婚是丈夫因无法容忍妻子的不同信仰而将其赶出家门的极小概率事件?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不使用其他资料,仅参考同一份记录簿,我们也可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比利牛斯山以外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夫妻的分手常常是由女方首先提出的,而且妇女主动离开她们的丈夫的现象非常盛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暂且不论,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蒙塔尤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典型代表性。
这种情况难免引起质疑,小范围细致化研究的结果能否作为确切的证据?《蒙塔尤》真的可以如作者期望那样折射出“我们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吗?这也许也是微观史面临的一个问题。
总之,《蒙塔尤》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而它所暴露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探究和思考。不管怎么说,这本书都是一部成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史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