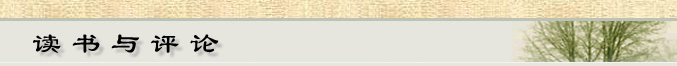正视国史特殊性
——
略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2006级本科生 姜畅
[提
要] 钱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他认为中国历史亦如其他历史一样,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钱穆先生在他有关于历史研究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深切的表现了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或历史落后于西方的地方,而正是这种特殊性是构成我们民族经久不衰的内在力量,是我们值得研究与探讨的关键。
[关键词]
特殊性;政治;经济;历史人物;文化
当我们回眸上世纪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时候,不能不看到梁启超和钱穆的卓越成就,他们各自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上世纪并立而行的重要史学理论著作,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今天读来仍有现实意义。钱穆(1895~1990),著名历史学家,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饱含深情而又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
80年代台北再版时增加《略论治史方法》和《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两文。这部书是钱穆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力作。此书乃汇集八次演讲而成,以主要意义分本演讲为八题,从通史和文化史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六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尤其清楚地看到,“钱老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爱护传统、尊重传统。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他强调中国文化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文化精神、历史走向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
并且,他一改以往认为中国历史发展落后于西方,甚至什么都不如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传统说法。
在本书的开篇中,钱穆就强调: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对于中国这个古老而闻名的古国,自然有我们自己的一套传统。
一、钱穆关于政治史特殊性的论断
“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从此段可以看出,钱穆对于中国的政治史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且对于中国人民的才智也是极为自信,我们姑且不去想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无丝毫的漏洞,只是社会藉此安定的几百年就使我们看到了此项制度的非比寻常。
但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近代科学上也的确如此。但对此,钱穆先生给予了极强烈的反驳,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治,如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赋税制度等,自然也是一种发明,这也恰恰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我们要做到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像孙中山先生那样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传统一笔抹杀。而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钱穆的此番论述实为给现代的中国人发出了警告: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若半身腰斩,盲目的学习他人,是不能有自己的主见的,这样下去,中国今后将永远无望。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应比较参照西方,追上世界的潮流,毕竟现在的事实就是西方的确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并且,西方国家建立的时间久,在制度上也在不断的完善,因此,其中有些制度自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亦不可数典忘祖,认识到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之所以能腾跃而起,并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而是有着强大的根基。而现在有针对性的创建一套逐渐完善的理论制度并且实践于现在的国情,那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二、从东西方对比品评我国经济史的特殊性
对于经济这一问题,似乎是最具现实性的问题,它不同于其他的几个方面,都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理解到一个高度,经济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尤其在今天社会,了解如何研究经济史似乎更有意义,更有引导国民思想的价值。
(一)人的欲望与经济发展都要适度
“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经济的水准若超过了人生所需的限度,对于人生则属不必要的,我们亦可称之为“超水准经济”,它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成为无用经济,只是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对于人的人生价值却无法提高。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是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经济观。早在《论语》中就提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说的恰中时弊。中国人的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因此,经济适度发展,对于人的追求及人生价值的实现,都是一种可贵的观点。与西方那种追求经济发展不平的传统观念截然相反。
在当今世界,经济确乎已成为判断一国实力的重要标准,作为物质基础,如果经济迟滞,那么其他的一切将无从谈及。但如果我们始终只是保持着一种“大同”的思想,使国民都同等的富裕,却都像现在的朝鲜一样,这样一种经济的发展也是值得商榷的。
(二)中国历代经济发展的高级目标——艺术化
中国古代,工商业其实是很发达的。“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这段精彩的论述,实为钱穆先生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体现。按照一般的说法,在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尽如人意的,然而,钱穆能打破这一常规抓住古代社会这一特殊现象并有理有据地让人信服,则实为一种别有创新的建树,让人不觉耳目一新,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燃起了研究的欲望。并且,以上的论断与现在的社会比较起来,实在是进步得多,同时,也让我们知晓了远古时代经济发展的高级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的艺术化。比如文房四宝、园亭建筑、道路桥梁等等,随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是放纵在牟利上。这是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特殊点,亦是我们值得骄傲之处。
(三)中西方经济史观的对比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的事。似乎是随着近代科技的兴起,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了,而现在的我们似乎一追再追,尽管有很大的超越,但仍免不了有落后之闲。而现代人对经济的适度发展观不如以前,于是,在如何使我们的经济重新赶超西方,并且标尺一种低水准状态,则是一值得研究大问题。关键就要看当代的中国人是否有敢于创新的精神。西方人从来就有一套浮士德式的无限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财力主义。他们一心想提高物质生活,但同时却也忽视了人生中其他有意义,有价值的选择,亦是漏洞百出。钱老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感慨:“中国今后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
对于西方的经济,国人一向采取盲目的追随,却往往忽略了到底应该追求些什么,殊不知西方的经济观也存在着缺陷。历史上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就完全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致命伤。因此,我们倒不如学习他们敢为人先、勤于创新的精神,那才是我们奋斗的真正武器。
三、“研究历史人物”之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钱穆没有像梁启超那样把人物专史置于其书诸种专史的首要地位,而是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讲才专谈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过,他与梁启超一样非常重视人的作用,尤其少数人的决定性作用。”在此讲中,他就直截了当地说: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了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
他重视人,尤其重视少数人的程度,与梁启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英雄史观的色彩浓厚得多。而他一独到的观点是很值得人深思的:在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辍,直到今天,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而依然存在。他在讲人物专史时更注重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理性地探讨人的历史和本质,凸显出人物专史的文化学研究特色。
相比于盛世的人物,他更重视衰世乱世的人物,颇有点“乱世出英雄”的味道,乱世英雄虽无事功,却能在事业之外表现自己,人性、人格更完美,更伟大,更可贵,也就发挥更大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同时,他更可贵的一点是不以成败论英雄,“成功者随事业成功而逝去,而失败者因事业的失败而长存。因为他们担负起历史传承的重任,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事业失败了,却为历史的前进开辟了道路,他们的事业与世长存,他们的影响和价值在后续的事业中得到实现,从而穿越时空而不朽。”人在事业上的不圆满,反倒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了。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有着驾驭一切的恢宏气度,是一般人做不来的;此外一点,是从无为中揭示有为,钱穆所讲的无表现的人物就是政治上无作为的人物,而这些人没有在政治上做出惊人的事业,却在其他方面大有所为,也就是无为而有为。实际上,
就是以此求出中国的史心,
求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
此外,他还指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亦是独特之处则在于,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还有贤人。……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们无所表现。
钱穆先生之于中国历史人物的专门研究,颇有道家的意味,不仅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浅谈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中国文化的延续
前面已提到文化史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贯穿全书的主线,亦是有关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的汇通,所有其中的这些研究论题都属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钱穆先生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可谓经典中之经典,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和作用。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能够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点而冶为一炉。但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同化力和包容性并不是其他文化所具有的。”这正是中国文化特殊性质所在。
他是把整个历史作为文化来看待的,文化是历史的真实表现和成果,并由此阐述历史的内涵和精神。这是大文化、广义文化,他的文化专门史也就是以此来定位的。他谈文化史研究方法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仔细地去划分文化史的种类和探讨文化史研究的具体方法,而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方法进行哲学和理性的思考,也就是说,文化研究要有哲学的眼光和头脑,研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所以,“也就能够进而对19世纪初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从文化心理、文化病、文化精神、文化交流与革新、文化共态与个性、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文化陶冶与修养、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批评。”
根据以上言论指出几种值得重视的方法: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辩异同。三、讨论文化须从大出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四、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出看。五、讨论文化应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且不去分析钱老对于文化的研究有无思想上的弊端,单单从他所指出的集中研究方法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文化是充满着自信的。他认为,中国文化能够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点而融为一炉。此外,他还认为,中国文化不但能容纳西方的宗教,也能容纳西方的科学,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决不会因西方科学的传入而受损。这种自信就是我们所常常讲的,文化的陶冶与修养,承担与护持。
“文化有共态与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当今我们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应在特殊处见长处,更不可只是看到别人的好,我们的就一无是处,当代人往往是缺少一种“文化精神”。钱老认为“中国文化到了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对于这句话我却不甚认可,如果要问什么才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经历上下五千年能够历久弥香,经久而不衰,实为世界之罕见。并且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性也是令世人瞩目的,当今的文化也并没有走到尽头,只是时代变化了,使我们的文化略感偏差,但是文化复兴的重任却正落在现代的国民身上,如果我们都是对自己的文化存在一种漠不关心、存心鄙夷的态度,那就真的是没有出路了。其实,在钱穆看来,文化的复兴并非是什么艰巨的任务,“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只要我们都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并且像样的做一个中国人,认真的扛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中华文化之复兴则指日可待了。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练来发扬,来持续。
《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部史学著作,给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研究方法外,还对中国历史及文化的特殊性做出了深彻的阐释。而这种特殊性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当然钱穆先生的思想会有过于肯定及褒扬我们的历史的地方,这种思想也贯穿于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当中,但正是他这种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史的研究,具有强烈现实感的精神,是中国精神传统真正的衔接,“他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和敬意,对未来的企盼和信心。”正因如此,正视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是我们研究与了解中国历史独特的财富。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2]
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3]
李木妙:《钱穆教授传略》,台湾: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4]
陈勇:《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6]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7]
柴文华:《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页。
肖建新:《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及方法论之比较》,《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陈曙光:《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陈曙光:《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