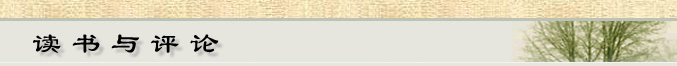|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读后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 陈超
妇女史在国内学界是一个已经兴起并处于上升趋势的学习和研究领域。不少学人正投身其中,边学习、边探索、边研究。其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尽管还不能称为成熟,但却正在逐步深入。相对于此,美国的妇女研究进行得较早,出现于 60 年代末期。在几乎同步的时间里(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就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产生了兴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女性视角的掌握和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在运用上比较娴熟。《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是笔者拜读的第一本北美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的专著。读后大获裨益,收获良多。
《闺》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之一,于2005年1月发行第1版。由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独撰,北大学者李志生翻译。高彦颐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东亚历史系博士,专攻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成果较为显著。李志生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卓有成效。
全书布局安排有中文版序、绪论、正文、注释、引文目录、索引、译者后记七部分。正文共有七章内容,分布于上、中、下三卷。全书约 33 万字,规模可谓不小。
一、基本内容
全书力图通过具体地展现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的上层妇女是如何生活的,来把握性别关系的互动,从而改写五四史观对传统妇女史的论述。作者认为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们在自身对儒家传统规定的妇女定位认同的情况下,在不断调整的儒家界限允许的范围内,或者说是在缝隙中求得了有限度的自由,她们不是无声的,她们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进而通过领会性别关系,向人们传达了一种更真实、更复杂的,有关中国的文化价值、它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变化本质的知识。
上卷名为“情史与社会秩序”,探讨了有关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为本书展开的背景,也是研究的基础。包含两章内容。第一章作者从繁荣的坊刻和出版业谈起,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客观地分析了女性读者兼作者的社会文化位置。第二章引入了“情”的概念,使用“浮世”一词不断强化社会的流动性,对“情”的关注,助长了妇女文化的发展,但作者强调“情迷”最终的社会效应是强化了“男女有别”的差异。
中卷名为“妇女性别的重写与重读”,在前面内容的基础上探讨扩大了的女性领域的构建,一些不平常的“职业女性”得以出现。并通过考察明清时人对女子的教育原理及内容,提出对女子特性的重新定义。这些内容分别于书中第三章和第四章阐述。
下卷名为“家门内外的妇女文化”,介绍了女性社团的四种变异:家居式、交际式、公众式以及名妓与职业作家和上层人士之妻的临时性社团。将黄媛介、王端淑、沈宜修、商景兰、顾若璞等典型妇女的行为作为个案研究,分别于书中的第五、六、七章中分析妇女文化的几种形式。
二、特色与借鉴
正像本书的“译者后记”中所写的译者在翻看此书之后“拍手称叹:叹其全新的视角,叹其深厚的功力,叹其优雅的表述”。对此笔者比较赞同。作者在叙述之始,以提问的方式“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么?”引出话题,接着回顾晚清、五四时期,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个较长时段内,从文学到历史研究当中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篇幅不算长,也没有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但提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与本书论题最相关的,且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以及陈东原的《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等作者与作品,勾勒出基本的观念问题:五四史观。作者认为在五四史观的影响下,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变得根深蒂固,之所以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这种混淆的出现,是因缺乏某种历史性的考察,即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处的世界。我不赞同‘五四'公式并不全因其不‘真实',而是‘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与其说是‘传统社会'的本质,它更多告诉我们的是关于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像蓝图。尽管此真理不无纤毫道理,但受害女性形象势不可当的流行,不但模糊了男、女关系间的动力,也模糊了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的运转动力。(p.4)作者在提出问题并分析其本质之后,不仅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接着还指出为了摆脱五四史观的传统,在研究中国妇女历史时“必须对特定的阶段和个别地区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最重要的是,妇女历史必须被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p.4)这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运用的方法和视角,以此来达到其写作此书的要旨:就是要“改写五四史观对传统妇女史的论述”。暂且不论作者对“五四”史观的看法是否得当和公允,至少她在书写之初即为下文的论述奠定了一个平台和基础,与读者之间有了一个约定。这种写法直接、清楚、醒目,可以使读者很快了解作者的意图。五四史观具有激烈的反传统色彩,有相当的进步性。但任何一种史观都不是完全的,一定有它的侧重和关注点。作者跳出五四情节,通过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才女文化进行研究,揭示出中国古代妇女生活的别样面貌,这一结论极具意义。
本书的关注点始终是:女性历史和明末清初的历史并行。也就是说把要考察的对象置身于一个整体的中国历史背景之下,将妇女史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中去解释,这一点在书中无论是从分析还是在谋篇布局中都被贯彻了。文章的第一部分探讨的就是有关明末清初江南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多的注意了经济的和文化的背景,较少涉及政治状况。尽管明末清初,有关系到改朝易代的重要政治事件,但作为妇女生活来讲,并不会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莫大的改变。百姓的日常生活总是在循序渐进中发生变化的。因此政治状况与本书的内容不直接相关,作者惜墨如金。而与本书的主题相关的背景,作者则用了将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笔墨,在描述坊刻的繁荣,和在涌现的阅读大众中的女性能见度时,不仅把货币和社会等级状况、印刷业的各种形式进行介绍,甚至还介绍书商的作用,以及书商在书前的头像插图和读者的关系,这种细腻而广阔的视野,使其背景具有网状的性质,而不是单一的。正是这些复杂的、多层面的情况,才能够在进行妇女史研究时真正做到“探索她们与中国历史的重新契合”(p.5)。而孤立地研究她们的隔绝也是没有意义的。
本书在方法论上能够自觉地避免简单化看问题。作者可以驾驭复杂问题,并做出复杂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地二分法。社会史的范畴之内有一些问题是模糊的,没有十分清晰而明确的界线,却也是真实的;有的甚至是矛盾的,却也都并行不悖地存在着。这往往给研究者的调查研究带来困惑。因为既要看到主要的潮流,也不能忽略次要的甚至是与其相反的方面存在,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客观事实。而这又容易使研究者在描述时出现困难,常常是列举了削弱自己结论的现象。而在这一点上,作者做的比较突出。运用的技巧相当成熟,书中多处可体现其功力之深厚。在考察“‘情'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人伦关系的首要位置”时,既提出受教育女性的不断增长,能够阅读和写作的女性数量上的逐渐增多,也没有夸大“情迷”的绝对社会效应,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能读擅写的女性的增加和她们助长的情迷,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一些女性享受着扩大了的自由和满足。但这些变化并未对明末清初社会性别体系的基本前提,即男女有别这一教条,造成挑战。”(p.117-118)对于印刷文化中女性的浮现这一现象,作者从多个角度去分析,认为“在个人层面上,一些女性在学问和文学的世界中,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在体制层面上则恰恰相反,对女性作家的推崇,反而强化了社会性别区分即‘男女有别'这一前提。”(p.70)从而得出的认识更全面、更客观,也更令人信服。作者在讨论“伙伴式婚姻”时,认为其是社会性别平等的有限实践,之所以“称其有限,是因为不管它带给相关个人的真实满足如何,但它并没有导致婚姻制度的正式变化,也没有对社会性别基础上的家内劳动分工进行重新组合。最终,‘金童玉女'这样一种浪漫形象,只能起到掩盖家庭中正式权力悬殊持久存在和夫妻间功能区分的作用。”(p.179)“‘良伴'和‘佳偶'等词汇虽然暗示着夫妇对等,但对伙伴婚姻的美化,最终还是强化了家庭和社会中的男女区分。”(p.195)“把寡妇自尽解释为殉情,并未减损鼓励寡妇守节这一道德说教的说服力。实际上,流行的伙伴式夫妻理想,很可能是节妇迷的一个原动力。没有对夫妻之爱的迷恋,就很难解释这样一种热情,带着这种热情,一些寡妇才可能接受了一种建之于否定她们性需要的意识形态。”(p.199)这些解释缀于长篇幅地描述“伙伴式婚姻”之后,既向读者传达了作者的信息:即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们创造出了一种怎样的生活的自由,同时也提示了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是不能对整个社会性别体系构成威胁的。这也许让读者会带有些许遗憾,但却是事实。
作者学术视野广阔,写作角度独特,女性视角、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运用娴熟。本书的作者高彦颐系 中国近代女性史研究专家、现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历史系教授 。历史学者如若能够广泛涉猎有关学科和专业里最突出、最前沿的学者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往往可以使自己研究的题目与切入角度是超出历史视野的。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获得不同于以往的认知。于是历史便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对我们业已熟知的历史带来修正和调整。中国史学界泰斗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他认为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学科都与历史学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都可以作为史学者的凭借。本书就可视为是对梁任公此种真知灼见进行实践的典型范例。作者借鉴了女权主义史学家琼· 凯利提出的对待女性史的“双重视野”、法国学者米歇乐·福柯的“无王的权力”概念、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支配的权力”、人类学家简·科利尔和西尔维亚·柳迫的批判。更重要地是将历史学家琼·斯科特提出的“社会性别”概念(《社会性别和历史政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成功地引入到明清史研究中来,并抓住关键“关注儒家经典著作和规训中,有关社会性别的规范性概念;在社会性别建构中,亲属制度和教育等社会制度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及明末清初上流妇女在她们自己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主观社会性别认同”。(p.6)作者的目标是要阐释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采用三重动态模式,即三种变化层面: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发现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即在官方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理想化准则与女性的自我视角相吻合的现象所“掩盖了通融的复杂过程和女性色彩斑斓的日常生活,它们经常是与官方准则相违背的”。(p.10)这种现象背后的真实是作者在具备了足够多学科的知识之后融会贯通,以转换后的女性视角再重新审视同一时段的历史得以获知的。这种别样的认知,更深化了作者对儒家传统的深刻理解:“只有我们停止视‘儒家学说'为抽象的信条或静态的控制机制时,儒家传统中妇女复杂、矛盾的生存状态才能够得到阐释。‘儒家传统'不是铁板一块和固定的价值、实践体系。无疑,作为一种哲学和一种生活方式,被制定于经典中的儒家意识形态信条,在漫长的历史中享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但同是它也有相当大的弹性。这一弹性是个别学者不断阐释经典的结果,透过这种适应和协商,他们将经典传统与变化的社会现实重新组合。在这层意义上,儒家传统与内 / 外界限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向通融开放的。”(p.19)“儒家传统在本质上动态和多样的。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看,儒家传统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秩序,一种对社会变化有着回应的秩序”。(p.21)这在笔者看来正是儒家传统的生命力所在。
三、存在的问题
但是本书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而严肃的,且不容忽视。尤为严重的是书中大量引用二手资料。这种做法有违历史学家的家法,削弱了作者论证的基础,进而减弱了论证本身的说服力和可信度。虽然二手资料并不是一定不能使用,但仅在说明别人的观点时方可。而要以此为基础来分析问题时,则必须要使用原始史料。因为进行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使用一手资料是其最基本的要求。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作者身为海外学人,其所具有的弹性思维、分析方式、驾驭复杂事务的能力以及文学修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弥补其史料掌握相对较差的不足。但太多地使用二手资料,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有待商榷甚至是错误的地方。这里仅举几例。如,书中在叙述社会文化背景之时谈到货币的购买力问题。作者举例“按1585年南京出版的律令之书所列出的商品价格,1两白银能买到3.2石米,或320斤盐,或80斤茶,或200张纸
,或400支毛笔。以工钱来看,从17世纪30—50年代,湖州一个中等农业劳动力在劳作一年后,除了可以得到全年的伙食外,还可得到5两白银。”(p.39)这个价格比在有一些明代经济常识的读者眼中看来是不可能的。而作者在注释中也写道“这个及其他工钱资料来自中山美绪(Nakayama),96—97页。有实例价格的律令之书名为《御制大明律例招拟折狱指南》(张秀民,《论文集》,148页)。对从明代注说和笔记中搜集到的食品和调味品价格的研究,参见杨永安,1:151—190页。亦请参见柯律格(Clunas),128—132页, 177—181页。”(p.317)作者在注释中详尽地注明了所用内容的出处,这一点是可取的。可仔细看来,作者所使用的资料有:日本学者中山美绪于1979年在《东洋史研究》中发的文章,张秀民于1988年出版的《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的成果,杨永安于1987年香港先锋出版社出版的《明史管窥杂稿》的内容,海外学者柯律格于1991年出版的《多余的东西: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身份》一书。这些均是现代学者对明代历史研究的成果,且不论这些研究的价值为何,也不论作者以此为研究得出的结论正确与否,仅是作者拿来这些研究成果作为自己的论断基础这种作法就是不可靠的,不足信,也不足取。对于这个价格比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则有待于笔者在调查原始史料后方可下断言。
作者在叙述叶绍袁时曾指出其先后担任“南京武学教授”、“北京国子监指导”和“工部秘书郎”诸官
职(p.200)。“国子监指导”与“工部秘书郎”名称未见于当时,据笔者调查叶绍袁的确切仕途经历为“授南京武学教授,改北国子监助教,升工部虞衡司主事”。(《中国方志丛书》之《吴江县志》卷三十一,“节义”,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p.920。)“指导”并非古代官职名称,在此借用实属不当,也不符合历史实际。“秘书郎”则早已有之,晋以后秘书郎一职归属秘书省,唐代秘书省下设有“秘书郎三人,从六品上。掌四部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貯。凡课写功程,皆分判。”(《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二》,p.1215)可见,秘书郎一职主要掌管艺文图籍之类的事务。而明代工部下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职,叶绍袁为虞衡司主事,职责是“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p.1760)与秘书郎之职所属事务相差甚远。而且,至明初,秘书监与秘书省之名全部废弃,其职责全部并入翰林院,秘书郎一职也不再设。因此,无论从名称还是从职务范围来讲,此处使用“秘书郎”一词确属错误。
书中第249页有一个图版,作者在图版下面有一段说明文字:“一位女性坐在轿子上,沿着西湖岸边去参加节日活动(周楫,《西湖二集》,晚明本;再印于长泽规矩也,《明代插图本图录》,44页)”。乍看上去,这一章正是书写女性的出游与户外活动,好像有了图版更能有个视觉的效应。但细细读来,图版上方有一段文字为“最恨无情芳草路,匿兰含蕙各西东”,从文字上来看应是叙述离别之情的,用于此处实属对史料的误读。
另有,本书作者的语言修为可谓高深,写作此书时也是怀有相当的激情。但也因此,有时出现推测的状况。“可能”、“似乎”、“好像”、“据说”等词语在书中常有出现。有些是为了下结论时更谨慎,有些则明显是证据不足。
尽管书中有诸多瑕疵,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写作之时,正是北美女性史研究的鼎盛时期,也是社会性别理论实践于各学科之时。其理论的成熟运用,研究女性的全新视角,以及提供的以具体了解妇女是如何生活为前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新方法,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中国传统妇女的单一的受压迫形象的明末清初的才女文化——她们是生机勃勃的,有自己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她们既是受压迫者,也是参与者。因此,高彦颐与她的著作《闺》书的成绩是确切的,是后人学者不可不读之著。当然,对于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客观视之,引以为鉴。
|